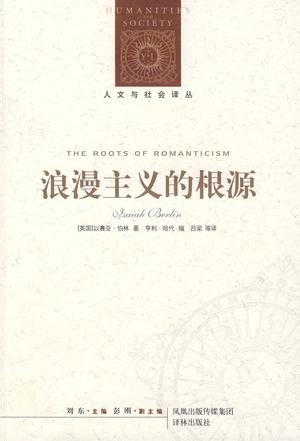
浪漫主义的根源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 …… [ 展开全部 ]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展开全部)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 收起 ]
[ 收起 ]
- 作者:[英] 以塞亚·伯林
-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 定价:18.00元
- ISBN:7544703991


登录 后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