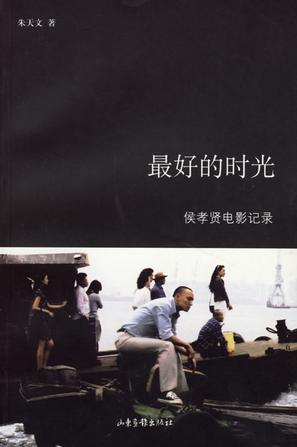-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僅僅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或許只有骨頭相同,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睫毛長些,個子高些,而且全身緊裹著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在我的世界則幾乎無一幸存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她幾近無知——卻堅守更高的目標。我遠比她見多識廣——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字跡清晰工整,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嗯,那首也許還不錯,如果改短一點,再修訂幾個地方。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時間在她劣質的表上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在我的表上則昂貴且精准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不帶一絲情感。她在消失的當下,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彩色條紋,我們的母親以鈎針為她編織的。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僅僅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或許只有骨頭相同,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睫毛長些,個子高些,而且全身緊裹著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在我的世界則幾乎無一幸存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她幾近無知——卻堅守更高的目標。我遠比她見多識廣——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字跡清晰工整,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嗯,那首也許還不錯,如果改短一點,再修訂幾個地方。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時間在她劣質的表上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在我的表上則昂貴且精准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不帶一絲情感。她在消失的當下,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彩色條紋,我們的母親以鈎針為她編織的。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僅僅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或許只有骨頭相同,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睫毛長些,個子高些,而且全身緊裹著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在我的世界則幾乎無一幸存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她幾近無知——卻堅守更高的目標。我遠比她見多識廣——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字跡清晰工整,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嗯,那首也許還不錯,如果改短一點,再修訂幾個地方。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時間在她劣質的表上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在我的表上則昂貴且精准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不帶一絲情感。她在消失的當下,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彩色條紋,我們的母親以鈎針為她編織的。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僅僅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或許只有骨頭相同,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睫毛長些,個子高些,而且全身緊裹著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在我的世界則幾乎無一幸存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她幾近無知——卻堅守更高的目標。我遠比她見多識廣——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字跡清晰工整,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嗯,那首也許還不錯,如果改短一點,再修訂幾個地方。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時間在她劣質的表上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在我的表上則昂貴且精准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不帶一絲情感。她在消失的當下,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彩色條紋,我們的母親以鈎針為她編織的。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僅僅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或許只有骨頭相同,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睫毛長些,個子高些,而且全身緊裹著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在我的世界則幾乎無一幸存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她幾近無知——卻堅守更高的目標。我遠比她見多識廣——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字跡清晰工整,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嗯,那首也許還不錯,如果改短一點,再修訂幾個地方。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時間在她劣質的表上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在我的表上則昂貴且精准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不帶一絲情感。她在消失的當下,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彩色條紋,我們的母親以鈎針為她編織的。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僅僅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或許只有骨頭相同,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睫毛長些,個子高些,而且全身緊裹著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在我的世界則幾乎無一幸存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她幾近無知——卻堅守更高的目標。我遠比她見多識廣——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字跡清晰工整,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嗯,那首也許還不錯,如果改短一點,再修訂幾個地方。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時間在她劣質的表上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在我的表上則昂貴且精准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不帶一絲情感。她在消失的當下,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彩色條紋,我們的母親以鈎針為她編織的。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僅僅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或許只有骨頭相同,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睫毛長些,個子高些,而且全身緊裹著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在我的世界則幾乎無一幸存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她幾近無知——卻堅守更高的目標。我遠比她見多識廣——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字跡清晰工整,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嗯,那首也許還不錯,如果改短一點,再修訂幾個地方。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時間在她劣質的表上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在我的表上則昂貴且精准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不帶一絲情感。她在消失的當下,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彩色條紋,我們的母親以鈎針為她編織的。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僅僅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或許只有骨頭相同,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睫毛長些,個子高些,而且全身緊裹著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在我的世界則幾乎無一幸存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她幾近無知——卻堅守更高的目標。我遠比她見多識廣——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字跡清晰工整,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嗯,那首也許還不錯,如果改短一點,再修訂幾個地方。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時間在她劣質的表上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在我的表上則昂貴且精准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不帶一絲情感。她在消失的當下,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彩色條紋,我們的母親以鈎針為她編織的。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僅僅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或許只有骨頭相同,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睫毛長些,個子高些,而且全身緊裹著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在我的世界則幾乎無一幸存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她幾近無知——卻堅守更高的目標。我遠比她見多識廣——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字跡清晰工整,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嗯,那首也許還不錯,如果改短一點,再修訂幾個地方。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時間在她劣質的表上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在我的表上則昂貴且精准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不帶一絲情感。她在消失的當下,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彩色條紋,我們的母親以鈎針為她編織的。至今仍留在我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