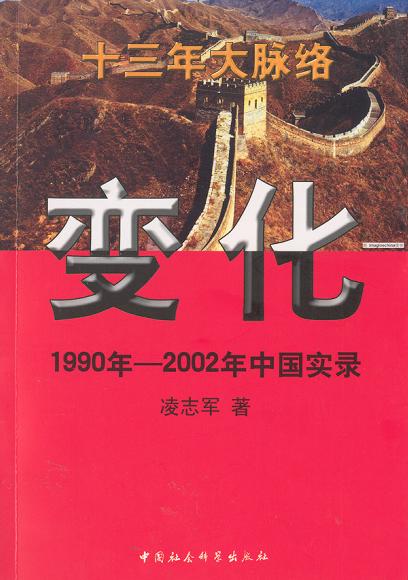查看所有书摘
按目录显示书摘
-
在迄今为止的岁月里,政府属下企业所遇到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自找的。政府举办的企业数以万计,在六百零八个行业中统治了六百零四个,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本身。党从执政的那一天开始,就认为只有国家所有的财产才能成为政权的基础,而一切民间资本都是异己力量,所以始终不遗余力地剪除私人资本,扩张经济中属于国家的部分。现在中南海终于明白,“这种局面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党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需要做大的做大,可以做强的做强,必须提高的提高,能够救活的救活,应该淘汰的淘汰,适合放开的放开,努力做到活有活的路子,死有死的办法。”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想方设法“搞死”自己的企业。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在迄今为止的岁月里,政府属下企业所遇到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自找的。政府举办的企业数以万计,在六百零八个行业中统治了六百零四个,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本身。党从执政的那一天开始,就认为只有国家所有的财产才能成为政权的基础,而一切民间资本都是异己力量,所以始终不遗余力地剪除私人资本,扩张经济中属于国家的部分。现在中南海终于明白,“这种局面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党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需要做大的做大,可以做强的做强,必须提高的提高,能够救活的救活,应该淘汰的淘汰,适合放开的放开,努力做到活有活的路子,死有死的办法。”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想方设法“搞死”自己的企业。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三十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他说的对。要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就不能只看1998年这一年。《交锋》也是因为迎合了这种需要,才格外风行。就其本身来说,它也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行文太激烈,爱憎太分明,实在不像很多人说得那样好,当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说得那么坏。人们用被夸张了的热情关注它,表达一种被夸张了的感受,无论褒贬,其实都是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这是政治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说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倾向,本来已经相当明显,而现在,有一股潮流涌出来,似乎是在与政治展开最后的热恋。乡下有人抗税,城里有人罢工,有人群聚起来上访告状,有人偷偷组织社团,法轮功的活动也是屡禁不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城市里,还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也是危险的。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厉有为的“社会主义”扬眉吐气了,站在他的对面怒目而视的另外那些“社会主义者”却在垂头丧气。他们煞费苦心地研究出那么多理论,批判了那么多人,坚信以往的失败只不过是受制于邓小平一人,既然邓小平已不在人世,中南海就会跟着他们走,“1992年以来”的一连串“悲剧”也将被颠倒过来。可是现在,1997年过去了,1998年就要来到,全中国热闹异常,他们却只好回到家中,除了指天骂地,就是枉自落寞,再往前看,还能做些什么呢?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官员依靠薪俸之外的利益维系其生活水准,在迄今为止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为制度所允许,而且是制度本身的一部分。它在90年代中期突然尖锐起来,以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缘于某种必然的逻辑。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向前推进,私人财富的积累开始分化,官员薪俸虽有增加,却无法追赶这种进程,其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又有极大的等级差别。多数官员的生活水准本来居于社会上层,现在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超过自己,诸如别墅、轿车、电话、飞机头等舱、火车软卧包厢这类东西,本来只有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现在也被别人分享。官员们若要在物质方面维护自己原来的位置,除了在黑白之间寻求回旋余地外,别无他法。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之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无第一代领导人集权集利号令天下的力量,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90年代中国的历史自有其饶有趣味之处,轰轰烈烈的事情常常不能持久,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银河号”事件当日闹得纷纷扬扬,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只是一个小插曲。既然历史在过去十几个月里发展得很快,那么自然,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掉转方向。毛泽东当年对年轻人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引起几十万人山呼海啸般地欢呼,可是现在,关心大事的人越来越少了。“那离我们太远了”,一个大学生这样说。“就让政治家们去关心吧。”年轻人嘲笑年长者的忧国忧民,开始构造自己的精神世界。“非意识形态化”的潮流悄悄地占领了他们的领地,当时也有人把这叫做“物质第一主义”。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那时候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的方针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事情是那些最多想象力和激情、最少传统理论约束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来的,但是很快就拓展开来。只需举出一个例证就可以知道,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那时候“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中国人进入90年代好几年了,可收入还不高。这一年,平均每个农民的收入只有七百八十四元,城市人比农民强得多,但也只有一千八百二十六元。上海人收入最高,三千一百五十六元,接下来就数上西藏了,它还排在广东、北京和天津的前边呢。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身边的穷人比富人多。当然遥远的地方穷人更多,那一年全中国还有七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二百元,有三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一百五十元,这些人全都住城里人一辈子也不去的地方,一辈子也不会到城里去。编辑们在报纸上公布他们的贫困和闭塞,就像描述富人的生活一样,用意明显:鼓励人们多挣钱。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现在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这一百八十公里的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那时候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的股票交易。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组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中国人真是有点怪,对于战场上的敌人———中日战争的、朝鲜战争的、中印战争的、中苏战争的、中越战争的,都可以握手言和,重建友谊,可是对于意识形态论争中的对手,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肯和平共处。就像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这头儿起来了,那头儿必然沉下去。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
-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这是当时人们分歧很大的问题。没有经历过当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变幻莫测的政治事件的人,不会理解这种争论在中国人的精神和感情方面所能引起的巨大波澜。这几乎是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所有大事的源头,牵涉着当时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如前所述,“左”的人士过了两年半的好日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掩饰对“左”的厌恶。昭阳说他们“无寸功于建设,却不断挥舞破坏的旗帜”。很多年以后万里谈到这些人,断然说:“中国的形势好不好,就看‘左’不‘左’。只要‘左’,就不行。”这个退休老人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一一历数“左派”劣迹,当然他也讨厌“右派”。他心目中的“右派”和别人所说的右派不是一回事。他说,“左”的人们到今天“还能自由自在,没有人批判,这是右了”。这条书摘已被收藏0次分享 收藏 0条评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