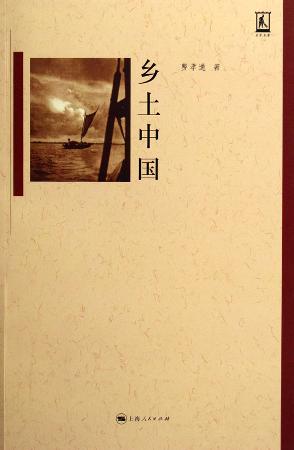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2-28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本书是刘春的“诗歌史”系列著作的第二部。沿袭第一部的整体风格,从论述柏桦、韩东、王家新、张枣、黄灿然等著名诗人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入手,揭秘新时期三十年风云激荡的诗歌江湖,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刘春
-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28.00元
- ISBN:9787549500819
-
1998年5月1日,韩东与朱文聊天,两人决定进行一次“大动作”,向全国数十个青年作家发出一份问卷,请他们回答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然后根据作家们的回答进行统计并形成文件公布出来,这就是后来引起文坛震动的“断裂”行为。随后的几天里,两人又与鲁羊多次商量,并草拟了问卷中的问题,最终决定该问卷由朱文作为发起人。
从5月12日发出问卷,至7月13日,共发出问卷73份,收回55份,加上朱文本人的答卷,共56份。随后,朱文对各个作家的答卷进行了统计,并写下了13则“工作手记”。《岭南文化时报》、《文友》和《街道》杂志相继发表了问卷的部分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反响,《南方周末》、《精品购物指南》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1998年10月,《北京文学》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为题发表了这56份答卷,以及作为附录的“问卷说明”、“答卷数据统计”、“工作手记”,还发表了韩东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等内容。以下为韩东的答卷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某一阶段的创作思想和对当今文坛的意见:
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
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
我对《读书》、《收获》两大名刊的评价是: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
我对《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两大权威选刊的评价是:如果作为最差小说的选本,它的权威性将不容置疑。
我对茅盾、鲁迅两大文学奖的评价是:如果作为当今最恶劣小说的奖项它的公正性有目共睹。
包括这份答卷在内的大部分作家的回答,因其辛辣、尖锐、偏激和决绝,在发表之后,引起轩然大波。文学界议论纷纭,叫好的、讨伐的、看热闹的不计其数。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互联网还远远称不上普及,但即使是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搜索一下“断裂问卷”这个关键词,仍然可以看到上千条相关新闻。
事实上,早在《北京文学》发表之前,朱文所写的“工作手记”,就已经列举出了在“行为”之初所引起的反应,在这里姑且引用几条:
一个北京作家收到问卷的当天打来一个热情洋溢的电话,高度赞扬了一番《断裂:一份问卷》,但是也说到自己的难处,在作协下属的单位上班,所以有些问题很难直接回答。
一些作家指责我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也有人说对被提问者带有某种侵略性。
上海一作家打来电话说,这件事很有意思,但是如果半途而废,就变成一次新闻炒作。一位朋友也劝告说,你们这样做,最终的结果将违背你们的本意,你们不知道,媒体是个怪兽。另一位朋友也说,你以前也不是这样,埋头写你的东西好了,管那么多干嘛,别人会认为你在沽名钓誉。更多的朋友善意地一笑,都什么年代了,还谈什么文学革命,太过时啦……
又有了一个说法。这次行为被描述成所谓的新生代作家企图取代什么代作家的一次集体行动,或者说,边缘作家不甘寂寞,开始争夺主流话语权力。
有一位作家还没有收到问卷,但是已经通过电话从其他作家那里知道了问卷的内容。这位作家抱怨说,千万不要寄给我呀。更为有趣的是,一位作家打长途电话给另一位作家,告诫他,答卷时小心点,因为你翅膀还没长硬……还有一些好玩的事情。不好玩的是,一份问卷甚至使多年的朋友因为意见相左而忽然感到隔阂起来。
作家的反应千差万别,而媒体的反应也相当“有趣”。行为开始时,很多杂志表现出对“问卷”的兴趣,然而,当杂志社的编辑收到问卷后,又显得忧心忡忡,担心出问题。有的刊物想发表,却提出条件,要求删去其中的一两个“敏感问题。”后来,内部出版的《岭南文化时报》刊出了这13个问题,却不知道是因为校对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出现多处错误。
最有意思的是“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穿一身绿衣服的人就像一只青菜虫子?”很多受到问卷的作家都以为提问者另有所指,是在影射什么。朱文为此先后收到十六个询问电话。深圳的《街道》杂志在刊出问卷的时候,也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会给办刊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坚持要删去。事实上,这个问题很简单,绝无“微言大义”。用朱文的话说,“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玩笑,也是对参加这次行为的作家填写答卷的一点谢意。灵感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个瘦瘦的朋友,他有一天忽然穿着一身绿衣服,只穿了一次就为他牢牢地赢得了‘青菜虫子’的绰号。”然而,面对那些纷至沓来的询问电话,朱文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解释和澄清。
从这些早期的反应,已可以预料到“问卷”在《北京文学》正式发表后的强烈“地震”。而韩东们并不打算就此偃旗息鼓,紧接着,韩东发表了《我的文学宣言》,宣布与腐朽的文学秩序进一步“断裂”。同时,他们开始策划“断裂”丛书。1999年3月,海天出版社出版了韩东主编的“断裂”丛书第一辑,收录了楚尘的《有限的交往》、吴晨骏的《明朝书生》、顾前的《萎靡不振》、贺奕的《伪生活》、金海曙的《深度焦虑》、海力洪的《药片的精神》六本小说集。在同时出版的《芙蓉》杂志1999年第二期中,韩东和朱文就“断裂”行为进行了一次长篇对话,对这次行动的目的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和阐释。随后,朱文撰写了《狗眼看人——从断裂丛书出版谈起》一文,再一次对这一行为进行思考,表明了立场。1999年5月出版的《芙蓉》第3期,韩东朱文、吴晨骏等人针对著名作家韩少功因为评沦家王干认为《马桥词典》有抄袭《哈扎尔词典》之嫌而将后者告上法庭并胜诉(文学界一般将此事简称为“马桥诉讼”),发起了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我仍这样说”行动。在这篇众多作家参与的对话中,哪怕对话者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并比较过《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词典》的异同,他们仍然在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后面用黑体字强调:“我仍这样说,《马桥词典》完全照搬《哈扎尔词典》;我仍这样说,《马桥词典》尽管广告满天飞,但仍不入流品。”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断裂”行为的延续。
2000年夏天,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汪继芳采写的“断裂作家”访谈录《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在书中,汪继芳对参加“断裂”行为的十三位南京作家进行了专访,并附录了相关资料。半年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楚尘主编的“断裂”丛书第二辑,收录了韩东的《我的柏拉图》、朱文的《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张旻的《爱情与堕落》、鲁羊的《在北京奔跑》四本小说集。
这一系列活动,把“断裂”行为的影响引入更深远的境地。
正如前文所说,“断裂”之后,各方面的反应十分强烈。据《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一书介绍,批评家王干与“断裂”行为毫无关系,但平时他与韩东等人接触得较多,被很多人认为是“断裂”分子,1998年11月下旬,王干参加“青创会”时,有人就在他的房门上张贴小字报,后来,王干的办公室还莫名其妙地着过一次火。更有意思的是,“‘断裂’使原本一团和气的南京作家们有了分别。原来作家们都是在一起踢球的,自从‘断裂’以后,作协那一拨人就不来踢了。”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柏桦兴奋异常:“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卸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下同)
紧接着,柏桦详细地描述了10岁的他莫名其妙地成为红小兵而融进“生活”之中的过程: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附近的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10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极端兴奋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
突然有人带头高吼:“冲市委啊!打倒某某!揪出某某!”人群开始向市委冲锋。
“这么多的敌人,暗藏的、现在的、历史的‘反革命’,但最大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还有反革命……”我正苦于连不起这黄昏的“新鲜”话语,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16岁,但我却觉得她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在那一瞬间,10岁的小男孩柏桦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人,仿佛国家的兴亡与自己密切相关。这种戴上了加速器的成长方式,牢牢铭刻在柏桦的记忆之碑上,令他难以忘怀,以至于33年后的1989年12月26日,他以诗歌的形式回顾了那个夏天自己的心理状况和社会景观: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抢军帽”开始流行了,大批判开始了,人性变得更为疯狂。“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地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情慌张,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最胆大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每一个孩子,当然也包括我,都在日以继夜地细查各种图案,其中一个惊呼:‘快看,这文具盒上的图案藏有反动口号。’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出,非常失落,看来那时我还真的缺乏某种超现实的眼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分件科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