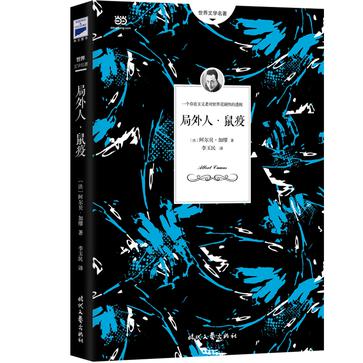在我所度过的这荒诞的一生中,一种捉摸不定的灵气,从未来的幽深之处朝我冉冉升起,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而这股灵气所经之处,便荡平了我生活得同样不真实的那些年间别人给我的各种建议。其他人的死亡,一位母亲的爱,跟我有什么大关系?神父的上帝,别人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跟我又有什么大关系?既然唯一的命运注定要遴选我本人,并且随同我也遴选像他那样自称我兄弟的千千万万幸运者。他是否明白呢?所有人都是幸运者。其他人也一样,有朝日也会被判处死刑。他也同样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他被指控杀了人,却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流泪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萨拉马诺的狗抵得上他的妻子。那个自动木偶式的矮小女人,跟马松娶的那个巴黎女人,或者跟渴望我娶她的玛丽,都同样有罪。雷蒙和比他更好的塞莱斯特,都同样是我的好哥们儿,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玛丽今天把嘴递给另一个默尔索,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这个也被判处死刑的人,究竟明白不明白,从我未来的幽深之处…
相当清醒。
明明刚才正在读鼠疫,却突然又想起局外人的这一段。
大家说的荒谬,在我看来却像随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所以在我看来不是荒谬,是冷漠…包括鼠疫也是一样,到了无法反抗时,就习惯了,就冷漠了…
只是大家面对的是鼠疫是不可抗力,我当年面对的是家庭,但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抗力。当然也可能只是我偷懒,放弃了永远朝一堵白墙做喊叫式的抵抗。但换做现在,即便心里知道还有很多的反抗方式,甚至可能有用,但我还是懒,不再想去动它分毫,因为改变自己总归还是比改变他人容易得多,我不想花费更多的时间跟不知道是他人还是自己继续拉扯了…
不知道再过多久之后,又会在这冷漠和荒谬中真的生出其他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