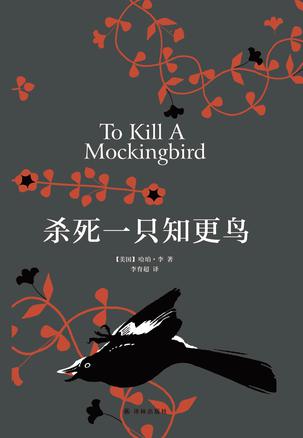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天晴得好像要过度了似的个个树叶绿到最绿的程度,朝阳似洗过澡在蓝海边上晒着自己。蓝海上什么也没有,只浮着几缕极薄极白的白气。
-
下了大雨。不知哪儿的一块海被谁搬到空中,底儿朝上放着。
-
那些基本条件,正如他心中那些美景,是朴素,安静,独立,能像明月或浮云那样的来去没有痕迹,换句话说,就是不讨厌,不碍事,而能不言不语的明白他。不笑话他的迟笨,而了解他没说出的那些话。他的理想女子不一定美,而是使人舒适的一朵微有香味的花,不必是牡丹芍药;梨花或是秋葵就正好。多咱他遇上这个花,他觉得他就会充分的浪漫—“他”心中那点浪漫就会通身都发笑,或是心中蓄满了泪而轻轻的流出,一滴一滴的滴在那朵花的瓣上。到了这种境界,他才能觉到生命,才能哭能笑,才会反抗,才会努力去作爱作的事。就是社会黑得像个老烟筒,他也能快活,奋斗,努力,改造;
只要有这么个妇女在他的身旁。他不愿只解决性欲,他要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合成一体的伴侣。不必一定同床,而俩人的呼吸能一致的在同一梦境
条小溪上,比如说里呼吸着。不必说话,而两颗心相对微笑。
-
他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没有无聊的争执,连无聊的诗歌也没有的世界;只有绿柳伴着明星,轻风吹着小萍,静到连莲花都懒得放香味的时候,才从远处来一两声鸡鸣,或一两点由星光降下的雨点,叫世界都入了朦胧的状态。呆立了许久,他似乎才醒过来。
-
想起幼时的迷信三十晚上,诸神下界。虽然不再
相信这个,可是除夕的黑暗确有一种和平之感,天尽管黑冷,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怖;街上的爆竹声更使人感到一点介乎迷信与清醒之间的似悲似欢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