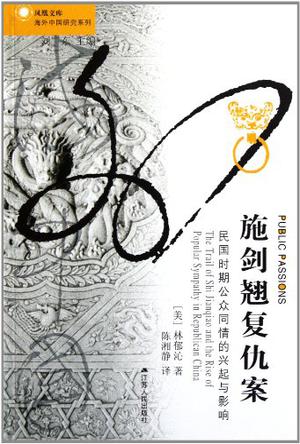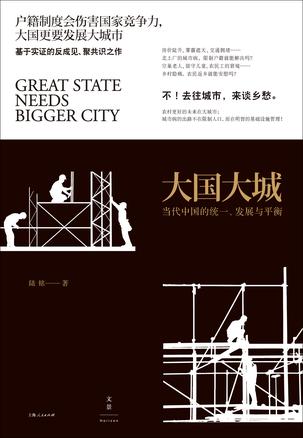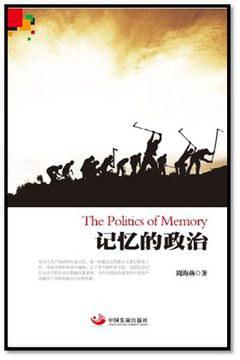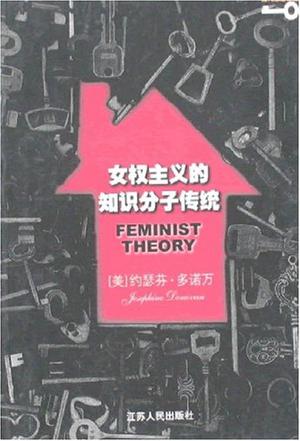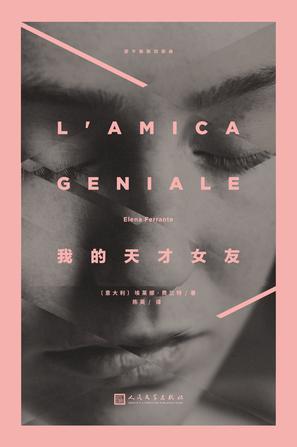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3-06
施剑翘复仇案
在《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中,林郁沁围绕着1935年施剑翘在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这一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林郁沁
-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 定价:26.00元
- ISBN:9787214074607
-
因此,在本书中,我不再追问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这一问题,而转向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批判性的政治参与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我试图说明,历史地来说,情感的道德真实性往往成为了比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沟通方式更为强大的规范性力量,驱动着集体的政治与。在20世纪中国,集体情感主义被证明是一种有力的、然而没有保障的、对于威权主义统治的解药。公众同情,特别是当它被自发地表达出来时,经常能成功地唤起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力批评。然而同时,他们也容易被操纵,并以一种可能导致灾难的方式爆发出来就这些矛盾而又深刻的后果而言,对30年代城市消费社会中兴起的、建立在“情”之上的公众进行历史审视,对于我们理解道德情感如何塑造了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的政治参与方式仍是有意义的。
通过指出以“情”为根基的公众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我并不是要表明中国对于西方的规范来说是一个特例。实际上,我的研究的另一个中心意图是从中国这个角度切入对现代性的普世主义叙述的解构,这一叙述在以“理性”为根基的公众中间仍然十分流行,这一理性公众在社会理论和学术研究中经常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经常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在应当是重新思考这一“理性”公众的时候了。正如传统儒家思想家所作的关于社会政治和谐的思考,我们难道不应该对情感领域如何使现代亻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进行更多的批判性思考吗?施剑翘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现代的女侠,展示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然而,正如本书开篇所说,熟稔媒体的女人和由大众参与的女性激情案例的出现并不仅限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同样,施剑翘案中展现出来的令人吃惊的公众激情的批判能量也许给现代中国之外的历史进程以更多的启示意义。 -
施剑翘的谋杀案虽然不是虚构的小说,却是一段关于法庭案件的通俗历史,这与金介甫讨论的犯罪小说有很多共同点。施剑翘的案子在关于民国的许多通俗历史中被讨论,这使得读者们能够旁敲侧击地去处理
当下时代的不公正。实际上,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亻的中国,关于解放前的中国的性、宗教、暴力等议题被认为是耸人听闻而又引人入胜的话题。对1949年之前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兴趣包括“寻根文学”中对乡土的留恋和对历史的追寻,以及如《红高粱》这样的“第五代”电影。与对过去的乡土社会的着迷相伴随的,是人们开始对民国时期的城市传奇和政治阴谋产生的新胃口,诸如《民国秘史》和《民国司法黑幕》这类书在书店的架上赫然出现。好些书名聚焦在著名的谋杀和奇特的案子上,包括《刀光剑影:民国暗杀记录》、《民国暗杀要案》(经1996)、《民国大案纪实》(经1997)、《近世中国十大社会新闻》(史1987)、《酒醉美人鱼:民国奇案》(朱1986)。这类对凶杀案的编纂中都会收入施剑翘的案子。《民国杀手春秋》包括了施剑翘本人的文章(施1994)。
-
我们已经看到,对这两个道德暴力案件的赦免最终对于政权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个层面上,国民党政权能够在特赦中施展它的行政力量,主张它新生活政权的地位,这一政权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德权威和武侠精神的基础上。政权利用特赦,把复仇者阐释为象征着“国粹”的新生活的英雄,他们的暴力复仇的行为能够给国家带来秩序。这些特赦还成为了政权用以展示其更高权威的“党义”的机会,并借此把自己描述成能够最好地传达大众情感、最能确保对正义的追求和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的力量。
然而,虽然这两个案子给政权提供了巩固权力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对这些暴力的认可也产生了也许令政权意想不到的后果。特赦的过程显示,凶杀案给政权内外的各种团体和组织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往往以牺牲中央政府为代价。市民团体把特赦作为申张他们自己的体制性影响力的机会。而表面上顺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客个人也抓住这次机会为他们达到个人目的创造空间。由于这些特赦令承认了公众团体所发出的请求的权威性,它们无疑给舆情赋予了力量,并使之与国家权威相区别开来。 -
尽管晚清时期的现代暗杀明确地指向清朝的国家政权,但到了民国时期,这一行为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政治暗杀不再有反国家的意义,而与政权自身联系了起来。学者们很早就发现,蒋介石有意识仿效着欧洲强大的法西斯政权来塑造国民党政权,这类政权都明里推行军国主义,暗中则制造着国家恐怖(比如方德万[ Van de Ven]1997)。像它的欧洲同伴一样,中国的政权试图制造恐怖的气氛,展览国家的控制力和暴力,并把它作为引人注目的权力的标志。它毫不犹豫地指使特务去暗杀那些它认为是阻碍了强有力的国家统治的政治敌人。
-
国民政府的话语中频繁地显露出两种需要之间的特殊冲突—民族国家既要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持续不断地发展和前进并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历史目的,又要把这个不断发展进化的实体落实在一个恒常不变的、永久的本质中。巴沙·查特吉( Partha Chatterjee)(1993)讨论了被殖民的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民族国家既看成一个在领土主权和政治定义上“现代的”国家,又看成一个在本质性的民族性格上“传统”的国家。查特吉( Chatterjee)以印度为中心,描述了男性民族主义者如何把真实的、纯洁的印度妇女变成了国家本质的典型象征。这些“纯洁的”印度妇女象征了一个内在的、精神性的领域,它隔绝于殖民者的存在并且不受他们的玷污。受这些理论家的启发,中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家们也把现代国家的进步和不变的永恒本质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放置在了女性的身体中(比如杜赞奇 Duara1998)。尽管他不像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把“家”和“家庭”神圣化,但他们确实对中国的妇女予以认可和褒扬,因为她们将自我牺牲的女性美德重新定位并导向了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公共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