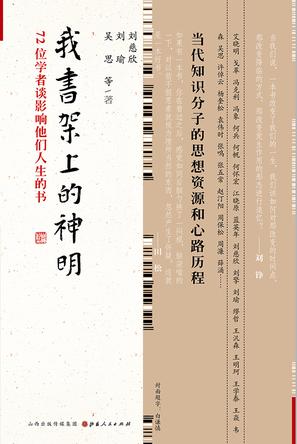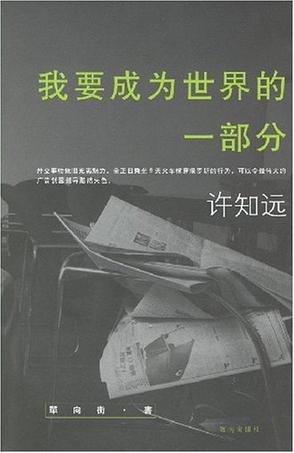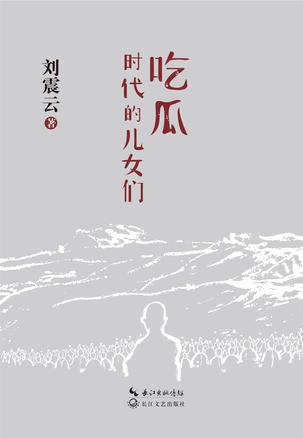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6-23
我书架上的神明
名人谈读书:
世上本没有经典,装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上面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刘慈欣 刘瑜 吴思
- 出版社: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 定价:CNY 58.00
- ISBN:9787203090342
-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2018-那些关于书的 朝闻道 阳历年的岁末,难得一个人寒夜枯坐,索性放下手边的具体事务,与日常里觉得的那个面目可憎索然无味的自我一起努力的回想-2018年那些关于书的记忆: 2018,大概是我读书以来年度买书最没节制的一年,海屯到需要剁手的程度。唯一聊以自嘲的就是,我之屯书是盗火者那般的囤积,已经绝版的二手的、盗印的也不嫌弃。我买书的行为真是没有一丝儿的矫情,不分线上、线下,不看淘宝、当当、亚马逊、互动出版,瘪下去的是腰包,满起来的是书架,大略算来,一年下来我给六百本书当了搬运工-一个中年油腻男早也过了小资的年龄。 2018,画了一个一喜一惧的大分号-六月里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标志着两亿字阅读量十年计划的收官,同时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一个延续至退休的六年阅读一亿字的补充计划-是否还能有六年的时光让我从容撷取?好在这六年的第一年里好歹也是完成了两千万字的计划量,没有欠账。 2018,我成功的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了。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全能的-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意识到对我这样的一般人这样的跨界是力不从心的。我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男,即使不能对人类知识的金库有所实际的贡献,但至少还是企望成为一个良匠,但现实中还需要练就一双慧眼,要能从刻意编造的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中发现那被掩盖阉割的真相,而我接受的自然科学训练并没有给我价值判断的能力。面对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需要我精通所有领域,这真不是泛泛如我般的资质可以支撑的,也就每每使我不能浸心于自己的志业,而敏感的心智又不能真的就视若无睹-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裂开的声音。 有那么几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人之必死性,我试着去接受阿伦特乐观的看法-正是人的有死性给看似无尽的恶政带来了希望的可能。曾用马丁.塞利格曼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提供的问卷做了次评测,对自己被评价为极度悲观并不意外,找来写作于1940年的《米塞斯回忆录》讲到卡尔.门格尔时的一段文字,“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此清晰地预见了灾难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事物的毁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绝望。古代修辞学者曾经认真考虑过,普利阿索斯王如果在二十岁时就已经预知特洛伊的灭亡,他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自己的特洛伊必然的灭亡之时,几乎还没有走完人生路程的一半。这种悲观主义吞噬了所有洞察明鉴的奥地利人。”那毕竟我还好-我至少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我确实悲观于自己的人生,但仍想活出它的亮度,即使它微弱的光亮只能照看跟前的些许空间,可能也会给同行人或后来人以帮助-这虽是向死而生的无奈但更是我的一种勇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