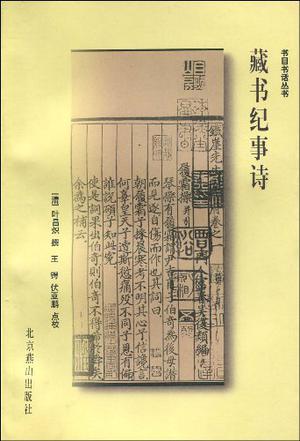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2-28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本书试图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如何在晚清到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这些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程美宝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定价:24.80
- ISBN:9787108024411
-
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下,在中国,地方文化的存在,绝对不会对国家文化造成威胁,正如客家人在强调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并不会阻碍他们表达自己的中国人或汉人的身份。中国文化定义本身所具有的弹性,足以包容为统治者或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地方或民族特色。在中国,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的特色,也就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广府话和客家话与国语大不相同,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广府或客家学人在讨论他们的方言特色时,就非将其与“中原”或“古音”扯上关系不可。中国的地方和民族文化既千差万别,又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地方学人的观念中,地方的差异性完全整合到理想中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去。简又文提醒人们,“广东文化”之谓,其实是“中国文化在广东”之意,一针见血地让我们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一体两面。如果“地方主义”有与中央分离之意,那么,“地方主义”绝对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地方文化观的主导思想。
-
由这些文人的经历及其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建树,我们意识到“文化”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观念。由此,我们有必要对从民国至今被读书人以至研究者们视为毋庸置疑的“地方文化”的意涵重
新做一点省思。 -
简又文和罗香林的经历也让我们想起了他们的前辈学者的经历。清末民国的广东学人,不少都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城市生活,与自己的家乡的联系是极为疏离的。对于学海堂第一、二代学长来说,广东在严格的意义上能不能算是他们的家乡,也值得斟酌。他们的祖父辈来自江南、浙江或福建等地,宦游或从商于广州,落籍于广州的附廓县番禺或南海。例如,本书第三章已经提到,学海堂最著名的学长陈澧,祖父辈是从江南迁到广州来的,父亲甚至因为没有落籍番禺,所以不能参加当地的科举,至陈澧一代才占籍为番禺县人。林伯桐先世由闽迁粤,遂世为番禺人;张杓祖辈为浙江山阴人,父游幕广州,杓入番禺县学为生员,遂为番禺人;张维屏曾祖自浙江山阴迁番禺,遂为番禺人;仪克中先世山西太平人,父以盐运使司知事分发广东,纳妾生子,克中奉母居番禺,遂为番禺人;侯康先世江南无锡人,祖父迁广东,遂为番禺人。(1)可以说,道咸年间像学海堂学长这类被认为是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一个真正本地的“根”,但他们却掌握着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极力为广东文化寻求正统性。(2)时至民国,像罗香林和简又文这一代学人,青年时期到上海、北京甚至外国留学,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来看,他们对于很“地方”的地方文化,并不见得有多少切身的体验。从晚清到民国的这些广东学人,大多以广州、香港、上海、北京这类大城市为他们的活动舞台,他们的地域文化观念,往往只能够托付在一省的层次上,才容易得到体现。就他们的仕途和事业而言,他们也往往处于国家与家乡的夹缝之中。在他们未能厕身中央的政坛时,他们回到广东,参与省内的政事;到他们无法影响政治时,他们又退到文化事务上去,掌握着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当他们无法定义当代的广东文化时,又回溯历史,界定广东过去的文化。在现实政治中失势,读书人只能凭借过去,为自己想象出一个当代的角色。联想到藏书文化,也深受江南一带的影响。
-
对于当时学海堂学者致力研究南汉历史的现象,麦哲维(steven miles)指出,此举除了表达了广东学人对本地文化历史的推崇之外,也显示他们借着这类课题的研究表现自己考据的功力。[1]曾钊(17931854)重新刊刻汉、晋、宋代省内外学者有关南方的记载。[2]谭莹(1800-1871)在行商伍崇曜的资助下,编纂了《粵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以及经过三十多年才完成的《岭南遗书》;[3]又为另一行商潘仕成将其私藏的善本编辑成《海山仙馆丛书》。[4]这些出版物收集了自宋以来广东文人的著作,丰富了广东文化的积累。这类印刷数量有限,商业价值不高的地方文化出版事业,如果没有商人的资助和高官的荫庇,自然难成其事。[5]
-
力是说明不了粵语的社会地位的。从上述讨论可见,粤语写作始终离不开娱乐、传道、教育妇孺的范围。尽管在很多场合里,粤语文本在家庭或乡村生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在中国人包括广东人的心目中,粤语写作的地位是属于边缘的,此尤以读书人为甚。中国方言繁杂,政府要达致有效的统治,必须发展出一套超越任何方言的行政语言,并为各地官僚和读书人所运用和接受。读书人也借靠着对这套语言的娴熟,表现出其对于政府以至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