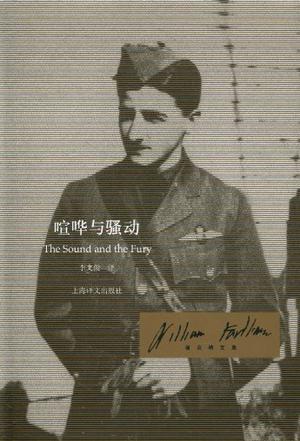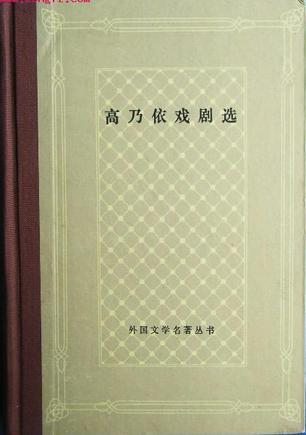-
理查德·瓦格纳曾说过,文明被音乐所消除,正如同光为日光所消除①。同样地,我相信,古希腊的文化人面对萨蒂尔合唱歌队会感到自己被消融了:而且此即狄奥尼索斯悲剧的下个效应,即国家和社会,一般而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鸿沟隔阂,都让位给一种极强大的、回归自然心脏的统一感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真正的悲剧都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释放我们,即是说: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拿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这种慰藉具体而清晰地显现为萨蒂尔合唱歌队,显现为自然生灵的合唱歌队;这些自然生灵仿佛无可根除地生活在所有文明的隐秘深处,尽管世代变迁、民族更替,他们却永远如一。
-
只有狄奥尼索斯狂热信徒的情绪中那种奇妙的混合和双重性才使我们想起了它,才使我们想到那样一种现象,即:痛苦引发快感,欢呼释放胸中悲苦。极乐中响起惊恐的叫声,或者对一种无可弥补的失落的热切哀鸣。
尼采的语言实在太精彩了!
-
无论是通过所有原始人类和原始民族在颂歌中所讲的烈酒的影响,还是在使整个自然欣欣向荣的春天强有力的脚步声中,那种狄奥尼索斯式的激情都苏醒过来了,而在激情高涨时,主体便隐失于完全的自身遗忘状态。即便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受同一种狄奥尼索斯强力的支配,也还有总是不断扩大的队伍,载歌载舞,辗转各地:在这些圣约翰节和圣维托节舞者身上,重又现出希腊人的酒神歌队,其前史可溯源于小亚细亚,直到巴比伦和放纵的萨卡人。如今有些人,由于缺乏经验或者由于呆头呆脑,感觉自己是健康的,便讥讽地或者怜悯地躲避④此类现象,有如对待“民间流行病”:这些可怜虫当然不会知道,当狄奥尼索斯的狂热者的炽热生命从他们身旁奔腾而过时,恰恰是他们这种“健康”显得多么苍白、多么阴森。
醉
-
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