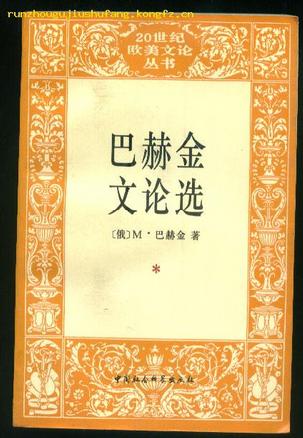-
“我跟你说,我非走不可!”我有点发火了似的反驳说,“你以为我会留下来,做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个机器人?——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能受得了别人把我仅有的一小口我嘴里抢走,把仅有的一滴活命水从我的杯子里泼掉吗?你以为,就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既没有灵魂,也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要是上帝曾给予我一点美貌、大量财富的话,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不是凭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凭着血肉之躯跟你讲话,一一这是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说话,就仿佛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两人一同站立在上帝的跟前,彼此平等,——就像我们本来就是的那样!”
第一次看到时,觉得简这段话说得真是太好了
-
“因为,”他说,“有时候我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一尤其是你像现在这样靠近我的候。仿佛我左肋下的哪个地方有一根弦,跟你那小小身躯里同样地方一根同样的弦难分难解地紧紧纠结在一起。一旦那波涛汹涌的海峡和两百英里左右的陆地把我们远远地分隔两地,我怕这根联系着两人的弦会一下绷断,那样我就会惴惴不安地担心我内心准会流起血来。至于你呢,——你却会忘得我一干二净。”
-
“除了额头,我看不出有什么妨碍幸福的结局,而这额头似乎公然在说:‘如果自尊和环境需要,我可以独自生活。我不必出卖灵魂去换取幸福。我有着与生俱来的内心财富,哪怕一切外界的乐趣全被剥夺,或者除非用我花不起的代价才能获得,它也足以支持我活下去。这前额在宣告:‘理智稳坐马鞍,牢握缰绳,决不会让情感像脱缰野马,匆匆将她带入深渊。热情尽可以任自己像那些真正的异教徒那样狂热发作,欲望尽可以海阔天空地想人非非,但判断力仍然在每一场争论中有最后的发言权,在每一个决定中投决定性的一票。狂风、地震、大火也许会在我身边发生,但我将始终听从那解释良心的命令的心灵之声的指引。’
罗切斯特先生看得很清楚嘛
-
她极爱卖弄,却毫无诚意。她外形很美,多才多艺,但她头脑贫乏,天性浅薄,任何花朵不会在那样的土壤上自动开放,任何无需强求自然结出的果实,也不喜欢这样的生土。她并不好,也并无独创的见解。她总是搬弄书本上的响亮词句,却从没讲过也不曾有过她自己的意见。她满口高调鼓吹高尚情操,却不知同情和怜悯之心为何物,温柔和真诚与她无缘。随时暴露出这一点的,是她常常无端发泄她对小阿黛尔所抱的恶意反感。要是阿黛尔偶尔走近了她,她就口出轻侮之词,把她一把推开。有时候她把她赶出屋子,平常对她老是态度冷淡尖刻。
-
“他在她们眼里跟在我眼里完全不同,”我想,“他跟她们不是同一类人。我相信他跟我是同一类的,一一我肯定他是,一一我觉得自己跟他相似,—一我明白他面容和举止中的含意。尽管财富地位相隔天壤,我的头脑和心灵、血液和神经中却有一种东西使我和他精神上彼此相通。几天前我不是还说过,除了从他手里接受薪金外我跟他毫无关系吗?我不是除了拿他当雇主外,不准自己对他有任何别的看法吗?这真是违背天性!其实我的一切良好、真诚、热烈的感情,都是围绕着他而迸发的。我知道我必须遮掩我的心情,我得抑制希望,我得牢记他不会太把我放在心上。因为我说自己跟他是同一类人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也有他那种对别人的影响力和神奇的吸引力。我只是说自己在某些志趣和感情上跟他有共同的地方。所以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之间是永远隔着一条鸿沟的。——但尽管如此,只要我一息尚存,知觉还在,我就不能不爱他。”
精神上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