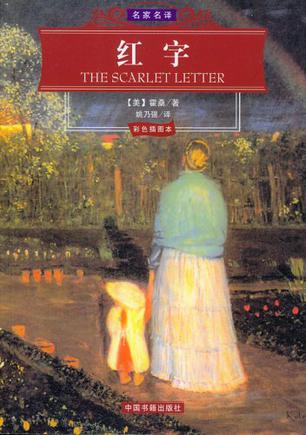我坐在联合国大厦的隔音室里,一边是即会当同声翻译也擅打网球的康斯坦丁,一边是满肚子习语的俄国姑娘,平生第一次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废物。问题是,我一直都是个废物,却从来没有自知之明。
我唯一擅长的是赢奖学金和奖品,这个时代快要结束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匹赛马,困在一个没有赛马跑道的世界上;或者像一名学院冠军队的橄榄球运动员,突然得西装革履地到华尔街去上班,家里壁炉台上一只小巧玲珑的金质奖杯是他往昔荣耀的缩影,奖杯上刻着日期,就像墓碑上的日期一样。
我看见我的人生像小说中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枝繁叶茂。
在每一个树枝的末梢,仿佛丰腴的紫色无花果,一个个美妙的未来向我招手,对我眨眼示意。一枚无花果是丈夫,孩子,幸福的家庭,另一枚是名诗人,又一枚是才学出众的教授,一枚是埃格,了不起的大编辑,再一枚是欧洲,非洲,南美,另一枚是康斯坦丁,苏格拉底,阿提拉以及一堆姓名古怪,从事非凡职业的情人们,再一枚是奥林匹克女队冠军,在这些无花果的上上下下还有许许多多我不大辨认得出的无花果。
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棵无花果树的枝桠上,饥肠辘辘,就因为我下不了决心究竟摘取哪一枚果子。我哪个都想要,但是选择一枚就意味着失去其余所有的果子。我坐在那儿左右为难的时候,无花果开始萎缩,变黑,然后,扑通,扑通,一枚接一枚坠落地上,落在我脚下。
扎心了……我甚至没能拿到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