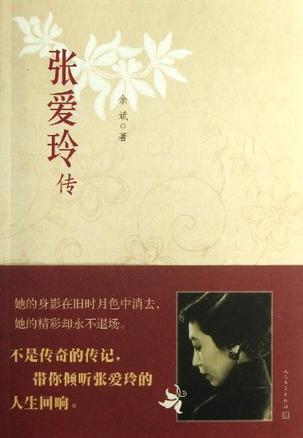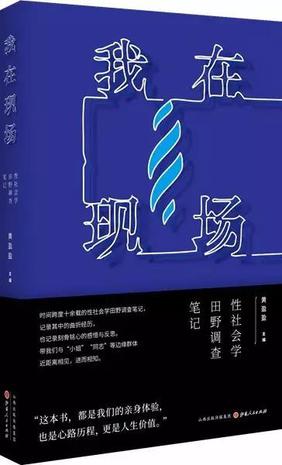-
佛朗士自然也把他的作风带到了课堂上。他对那些枯燥乏味的教科书以及四平八稳的历史书显然是不满的,“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 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从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她曾说:“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私下里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而她在佛朗士这里听到了。佛朗士的授课即使对张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启迪和支持了她后来的态度:“清坚决绝的字宙观 ,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张爱玲称学生(当然也包括她自己)从佛朗士那里“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并且说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她在文章里还很少对别人表示出这样的敬
意。
这位教授讲的是哪一段历史,他究竟向他的学生灌输了怎样的思想,这些都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也点明了张爱玲把握、认识人生的独特方式以及人生观构成上的特点。她厌恶理论,并不追求观念上的自相一致,而希望在对历史、人生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之间求得平衡与统一。所谓“扼要的世界观”,作为对人生、对世界的粗略看法,本身也许分量不够,却因为有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切感受做底子而显得丰厚。在粗略的一条条看法之间,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维持着活跃的演出,貌似矛盾的见解皆消融、调和于深切的感受以及对现实的态度之中。唯其如此,人生观对张爱玲具体而微,几乎是一种可以触到、见到、嗅到的不失感性生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