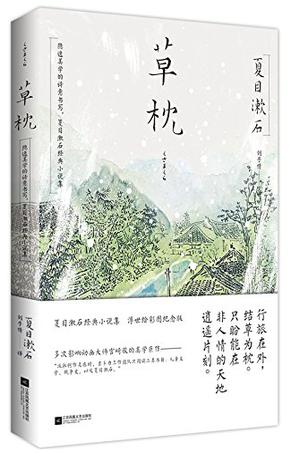此书摘本创建于:2016-06-09
罗生门
本书不仅收录了《罗生门》《竹林中》《地狱变》《河童》等最广为人知的经典名篇,同时精选了《英雄之器》《南京的基督》《丝女手记》《枯野抄》等国内罕见译作,共28篇。由黑泽明 …… [ 展开全部 ]
- 作者:芥川龙之介
-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 定价:68.00元
- ISBN:9787222132405
-
唯有这样来到不知名的深山野岭,将五尺瘦躯埋藏在迟暮的春色中,我才终于明白真正的艺术家应有的态度。一旦进入这种境界,美的天下尽归我有。纵然不染尺素,不涂寸缣,我照样是第一流的大画家。饶是在技巧方面不及米开朗琪罗,在精致程度逊于拉斐尔,但在艺术家的人格方面,我与古今大师齐首步武,没有丝毫逊色之处。自从我来到这个温泉区,迄今一幅画也没画,甚至感到画具箱只是一时兴起扛出来好玩的。旁人或许会嘲笑我这样也配算是画家。然不管别人如何嘲笑,现在的我就是真正的画家。是地道的画家。得到这种境界的人,不一定会画出名画。但是能够画出名画的人必然得知道这种境界。握着画笔不能成为画家,提着菜刀不能成为厨师,捏着钢笔不能成为作家。即便握着画笔在画架上绘作,那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画画的人。西方有位著名的领导人曾经说过“力量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主人。”一个人只是依靠画笔和画架去画画上成不了画家的,“家”这个字是有掌握的意思在里面的,必然要在所踏足的这一方天地反客为主才敢承担。不是在画架上画出来才是画,目光所及,心中自然展现出美好之景,即便不动笔不染色,依旧是高超的画家。
-
汉大将军吕马通将一张马脸拉得愈发之长,捋着几茎稀稀拉拉的胡须说道。他身旁有十余人,中间一盏灯火,将一张张脸孔映得通红,衬托在夜晚的营帐上。每张脸上,都浮现出难得一见的笑容。想必是今日一仗,取下西楚霸王的首级,得胜的喜悦还没消失的缘故吧。
“是吗?”
其中一张脸孔,鼻梁笔挺,目光锐利,嘴唇上浮出不屑的笑容,盯着吕马通的眉心应了一声。不知为什么,吕马通似乎有些狼狈。
“当然,项羽力大盖世。听说连涂山禹王庙的石鼎都能折断。今日一仗也是如此。一时之间,在下以为要性命不保。李佐被杀,王恒被杀。那气势,真个无敌。确实力大盖世。”
“呵呵。”
对方脸上依然不屑地笑着,鹰扬威武地点了点头。营帐外,寂然无声。远处,响起两三声号角,此外就连马的鼻息都听不到一丝。这时,不知从何处飘来枯叶的气味。
“然而,”吕马通环伺所有的面孔,煞有介事地眨了一下眼睛。“然而,确非英雄之器。证据,便是今日之战。楚军败退至乌江畔,仅剩二十八骑。面对敌军如林,虽战,亦无济于事。据闻乌江亭长曾驾舟前去接应,本可退至江东。倘项羽确为英雄之器,当忍辱渡江,待他日卷土重来。岂可因小失大,为区区面子而耿耿于怀!”
“照此说来,英雄之器者,乃工于算计之谓乎?”众人随即异口同声笑将起来。然而,吕马通毫不气馁。略挺一挺胸脯,不时瞥一眼那张鼻高目利的面孔,比手画脚,振振有词道。
“非也。非此意也。曾闻项羽其人,于今日开战之前,对二十八名部将说过:‘此天之亡我,非人力之不足也。以现有之兵力,必三胜汉军,当令诸君知之。’诚然,岂止三胜,实为九战九胜。但依在下之见,此乃怯懦之言。将自家之失败,归咎于天——老天岂不困惑至极!项羽此话,倘系渡过乌江,纠集江东健儿,再度逐鹿中原之后所说,则又另当别论。然而,事情恰恰相反。本可活得轰轰烈烈,却自蹈死路。在下谓项羽非英雄之器者,并非仅因其不工于算计。将成败委诸天命,以为搪塞,则万万不可。萧丞相这等饱学之士如何说,在下虽然不知,但窃以为,英雄者,决非此等人物。”
吕马通面带得色,环顾左右,一时缄口。众人也许认为言之有理,彼此轻轻点了点头,沉默不语。不料,唯有其中那张高鼻子面孔,眼中突然现出感动的神情。黑眸子热辣辣地闪闪发亮。
“当真?项羽说过此话?”
吕马通将一张马脸上上下下大大点了两下。
“岂非怯懦?至少,非大丈夫之所为,窃以为,英雄者,乃敢于天斗之人也。”
“不错。”
“知天命,犹与天斗,方为英雄。”
“不错。”
“如此说来,项羽……”
刘邦抬起一双目光锐利的眼睛,凝神望着秋风中闪烁不定的灯火。隔了一会儿,自言自语似的徐徐说道:
“真一世之英雄也!”吕马童认为项羽归命于天是怯懦,刘邦也同意知天命与天斗才是英雄,但为什么两个相似的观点最后发生了分歧?这一点我是很没有看懂芥川的逻辑,大概芥川认为,若项羽认为天命已去,那么自刎或许就是自我摆脱天命?我们设想三个结局,要么就是渡江再战而胜,要么就是渡江再战而亡,要么就是当下自刎。第一种结局大概率不可能实现,第二种结局就代表项羽又被天命玩弄了一遭,因此第三种结局就是摆脱天命玩弄的最佳方式,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最后的奋力一争? -
大公说到这里,向旁边的人递过一个眼色,然后换成阴郁的口气说:“车子里捆着一个犯罪的女子,车子一烧,她就得皮焦肉烂,化成灰烬,受最后的苦难,一命归阴。这对你画屏风,是最好的样板啊。你得仔细观看,看她的雪肤花容,在火中焦烂,满头青丝,化成一蓬火炬,在空中飞扬。”
火焰逐渐包围了车篷,篷门上紫色的流苏被风火吹起,篷下冒起在黑夜中也显出白色的浓烟。车帘子,靠手,和顶篷上的钢绞链,炸裂开来,火星像雨点似的飞腾……景象十分凄厉。更骇人的,是沿着车子靠手,吐出万道红舌、烈烈升腾的火焰,像落在地上的红太阳,像突然迸爆的天火。刚才差一点叫出声来的我,现在已只能木然地张开大口,注视这恐怖的景象。 良秀那时的脸色,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当他茫然向车子奔去,忽然望见火焰升起,马上停下脚来,两臂依然伸向前面,眼睛好像要把当前的景象一下子吞进去似的,紧紧注视着包卷在火烟中的车子,满身映在红红的火光中,连胡子碴也看得很清楚,睁圆的眼,吓歪的嘴,和索索发抖的脸上的肌肉,历历如画地写出了他心头的恐怖、悲哀、惊慌,即使在刑场上要砍头的强盗,即使是拉上阎王殿的十恶不赦的罪魂,也不会有这样吓人的颜色。甚至那个力大无穷的武士,这时候也骇然失色,战战栗栗地望着大公。
可是大公却紧紧咬着嘴唇,不时恶狠狠地笑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个场景。在车子里——啊啊;这时候我看到车中的闺女的情形,即使到了今天,也实在没有勇气讲下去了。她仰起被浓烟问住的苍白的脸,披着被火焰燃烧的长发,一下子变成了一支火炬,美丽的绣着樱花的宫袍——多惨厉的景象啊!特别是夜风吹散浓烟时,只见在火花缤纷的烈焰中,现出口咬黑发,在铁索中使劲挣扎的身子,活活地画出了地狱的苦难,从我到那位大力武士,都感到全身的毫毛一条条竖立了起来。
一阵像黄金果似的火星,又一次向空中飞腾的时候,猴儿和姑娘的身影却已埋进黑烟深处,再也见不到了。庭院里只有一辆火烧着的车子,发出哄哄的骇人声响,在那里燃烧。不,它已经不是一辆燃烧的车,它已成了一支火柱,直向星空冲去。只有这样说时,才能说明这骇人的火景。
最奇怪的,——是在火柱前木然站着的良秀,刚才还同落入地狱般在受罪的良秀,现在在他皱瘪的脸上,却发出了一种不能形容的光辉,这好像是一种神情恍惚的光。大概他已忘记身在大公的座前,两臂紧紧抱住胸口,昂然地站着,似乎在他眼中已不见婉转就死的闺女,而只有美丽的烈火,和火中殉难的美女,正感到无限的兴趣似地——观看着当前的一切。“
奇怪的是这人似乎还十分高兴见到自己亲闺女临死的惨痛。不但如此,似乎这时候,他已不是一个凡人,样子极其威猛,像梦中所见的怒狮。骇得连无数被火焰惊起在四周飞鸣的夜鸟,也不敢飞近他的头边。可能那些无知的鸟,看见他头上有一圈圆光,犹如庄严的神。
鸟犹如此,又何况我们这些下人哩。大家憋住呼吸,战战兢兢地,一眼不眨地,望着这个心中充满法悦的良秀,好像瞻仰开眼大佛一般。天空中,是一片销魂落魄的大火的怒吼,屹立不动的良秀,竟然是一种庄严而欢悦的气派。而坐在檐下的大公,却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口角流出泡沫,两手抓紧盖着紫花绣袍的膝盖,嗓子里,像一匹口渴的野兽,呼呼地喘着粗气…… -
卢生心想自己就要死了。眼前一片昏暗,子孙的啜泣声渐渐飘远,脚上似乎坠着一个无形的秤砣,身体一点点地向下沉…就在这时,他蓦然惊醒,不由得大睁双眼。
凝神一看,道士吕翁仍然坐在他的枕边,主人煮的黄米饭,似乎还没有熟。卢生从青瓷枕上抬起头,揉着眼睛,打了一个大呵欠。邯郸的秋日午后,虽有阳光照在落叶的树木梢头,仍令人感到些许寒意。
“你醒了?”吕翁咬着胡须,强忍住笑意,问道。
“唔。”
“做梦了吧。”
“做了。”
“梦见什么了?
“是个很长的梦。一开始,我娶了清河崔氏的女儿,似乎是个容姿美丽、端庄有礼的姑娘。第二年,我进士及第,授官渭南尉,之后,又升至监察史、起居舍人知制诏。再后来,我官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却为谗言所害,几乎丢了性命。好不容易逃此劫难,被流放驪州,在彼处约莫过了五六年。最后,冤屈终于得以昭雪,我又被召还回朝,官居中书令,封爵燕国公,此时已经颇有年纪了。有子五人,孙辈则有数十人之多。”
“后来呢?
“过世了。寿数似乎八十有余。
吕翁得意地捋着胡须。
“那么,荣辱之道,穷通之运,你也大略体会过了罢。这就是了。人生在世,与你梦中所见并无丝毫分别。如此一来,我想,你对人生的执着与炙热之心当有所冷却。知晓了得失之理、生死之情,再看人生,终究也无甚意味。你说是也不是?”
听着吕翁的话,卢生脸上现出焦躁的神色,当吕翁叮问他最后一句时,他扬起年轻的脸,双目灿灿生辉,答道:
“正因为那是梦,所以我还想好好活一回。正如彼梦会醒来般,此梦也终有梦醒之时。在梦醒之时到来以前,我想真正地活回,要活得不虚此生。老丈以为如何?
吕翁只是皱着眉头,既没有答“是”,也未曾说“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