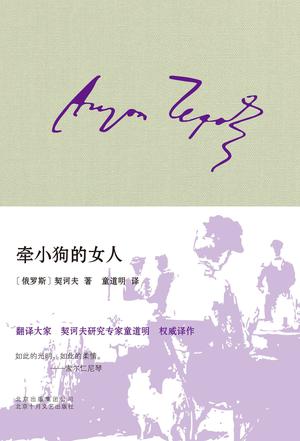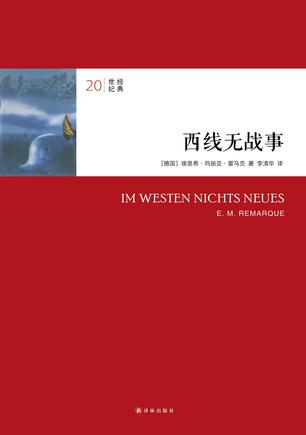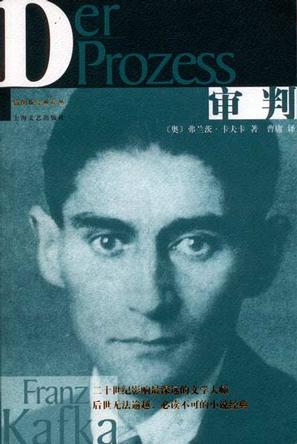-
〔他是有他的难言之痛的。
〔早年婚后的生活是寂寞的,麻痹的,偶尔在寂寞的空谷中遇见了一枝兰,心里不期然而有憬悟。同声同气的灵魂,常在静默中相通的,他们了解寂寞正如同宿鸟知晓归去。他们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得了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不互通款曲。士大夫家庭原是个可怕的桎梏,他们的生活一直是郁结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他们只沉默地接受这难以挽回的不幸,在无聊的岁月中全是黑暗同齟龉,想得到一线真正的幸福而不可能。一年年忍哀耐痛地打发着这渺茫无限的寂寞日子,以至于最后他索性自暴自弃,怯弱地沉溺在一种不良的嗜好里来推毁自己。
〔如今他已是中年人了,连那枝幽兰也行将凋落。多年瞩望的子息也奉命结婚,自己所身受的苦痛,眼看着十七岁的孩子重路覆。而且家道衰弱,以往的好年月仿佛完全过去。逐渐逼来的窘,使这懒散惯了的灵魂,也怵目惊心,屡次决意跳出这窄狭的门槛,离开北平到更广大的人海里与世浮沉,然而从未飞过的老乌简直失去了勇气再学习飞翔,他怕,他思虑,他莫明其妙地在家里踟蹰。他多年厌恶这个家庭,如今要分别了,他又意外无力地沉默起来,仿佛突然中了瘫。时间的蛀虫,已逐渐啮耗了他的心灵,他隐隐感觉到暗痛,却又寻不出在什么地方。 -
〔她的丈夫曾文清,由右边卧室门踱出——他是个在诗人也难得有的这般清俊飘逸的骨相:瘦长个儿穿着宽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举止谈话带着几分散模样。然而这是他的自然本色,一望而知淳厚,聪颖,眉宇间蕴藏着灵气。他面色苍白,宽前额高骨,无色的嘴唇,看来异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悲哀而沉。时常凝视出神,青筋在额前边凸起。
〔他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下棋,赋诗,作画,很自然地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的时间。北平的岁月是悠闲的,春天放风等,夏夜游北海,秋天连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在霁雪时的窗下作画。寂寞时排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半生都在空洞的悠忽中度过。
〔又是从小为母亲所溺爱的,早年结婚,身体孱弱,语音清虚,行动飘然。小地方看去,他绝顶聪明儿时即有“神童”之誉。但如今三十六岁了,却故我依然,活得是那般无能力,无魂魄,终日像落掉了什么。他风趣不凡,谈吐也好,分明是个温厚可亲的性格,然而他给与人的却是那么一种沉滞懒散之感,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种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虽然他很温文有礼的,时而神采焕发,清奇飘逸。这是一个士大夫家庭的子弟,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结果。他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