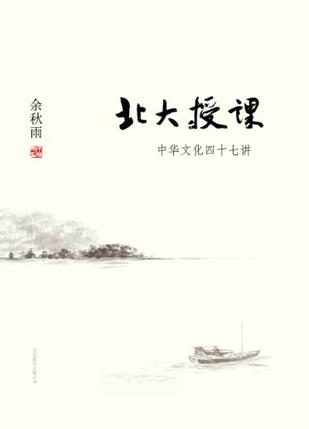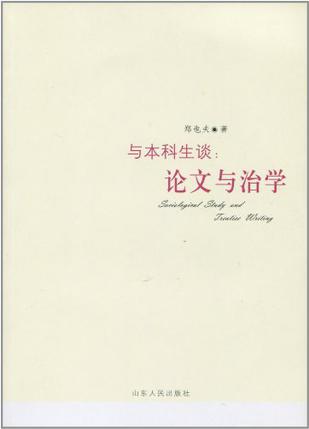-
封建的“礼教”和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与封建礼教结合在一起的“入世”精神和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都不能不承认在当时仍有其积极意义。从一个方面看,中国传统“入世”精神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现实社会,要求人们重视现实的人生,从这方面看是有利于无神论思想的发展。
-
怪力乱神”等非常赞赏。他批评佛教宣扬天堂地狱、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等都是虚无缥渺、荒诞不经无法证实的说教,追求一些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可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则主张士大夫应注重立身扬名,身体力行周孔的道德教化,切切实实做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何承天在《重答颜光禄最后说:君子“处者弘日新之业,仕者敷先王之教,……何必陋积善之延祚,希无验于来世;生背当年之真欢,徒疲役而靡归,系风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违通人之致。”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比起佛教教义来有什么可以肯定的地方,何承天所提倡的这种“处者弘日新之业,仕者敷先王之教”的积极入世态度,则是应该肯定的。
-
中国古代思想和印度佛教相比较,其最大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一贯把“治国平天下”作为其实现的目标,因此它的精神是“入世”的,而佛教则认为世界是一大苦海,要求超脱现实社会,因此它的精神是“出世”的。《弘明集》是梁朝和尚僧祜编的一部弘扬佛法的文集,其中有不少文章讨论到沙门应不应礼敬王者、孝养父母的问题,它不仅收录了僧人们对这一间题的文章,也收录了对佛教徒在这一问题上的批评文章。在《弘明集)卷十二中有庾冰的《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和桓谦《答桓玄论沙门敬事书》等文。前者指出,佛教徒见君主不行晚拜之礼,是违反“名教"的。后者指出,佛教徒削发为僧,违背了养亲的孝道。而桓玄下令沙汰沙门的理由则是:“京师竟其奢浮
-
“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王弼《齐物论》
-
“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王弼《齐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