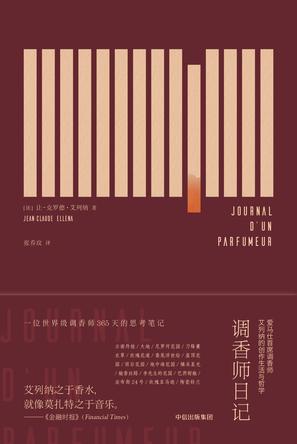-
邻家草皮总是比较绿
2010年2月15日,星期一,莫斯科因为“爱马仕之旅”的发布会,我来到莫斯科。当我在大厅坐定,向旅馆服务生要了一杯红茶,她送来埃迪亚尔( Hediard)精选茶。我若在巴黎同一等级的旅馆,他们会端上俄国品牌的库斯米茶( Kusmi tea)。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甚是,“资本主义就是,”他写道,“一种交换游戏。”
-
焦虑是旧识,一向不请自来。它在我二十岁或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冷不防冒了出来。我先是厌恶,继而接受了它。拜它所赐,我后来明了何谓“世间真正的谜都是双眼可见,而非不可见的”。读到王尔德这句既简单又复杂的话,令我动心骇目,有种脚下虚浮了几秒的感觉。我瞧见自己脚下开了深渊大洞,知识全都不见了;紧接着又为这一刹那的错觉赞叹起来,因为它见识了我内心惊醒,证实了我的确存在。焦虑通常毫无预警就会冒出来,但是我认得前兆。它最常在创造香水起步的时候显现。我有时读着刚写下的配方头几行,就内心焦灼起来。配方虽然只有短短数行,却令我五内生惧,心慌又担心自己计穷智短,文思枯竭。其实我感到一股野兽般的需求,想要—一容我这么说“光着身体”去创作,好像把堆满创作者,特别是经验老到的创作者,那些生命的自发性、条件反射都“脱掉”。这头几行有时纯属热血冲头的产物,发自昙花一现的欲念,但往往是为了较为广泛周延的计划而写。我必须用我的意图和欲望来包装这几行屡屡让我恐慌的字。
另一种焦虑在我创作某支花园香水时缠上我。我调配这支香水的做法,不是把抽象的想法具体化,而是看我身在何处,要选择什么内涵。面对这么多可能性,挑选一种或多种能变成符号的气味,形同走上一条我得自己开辟的路;选择越多,焦虑越发强烈。为此我
失眠了好几夜。有人或许会反驳我,说这是我自寻苦头,未必人人如此,我很乐意受教。但我依然相信经济的交流使得品味亦即嗅觉变得整齐划一,你我会共享某些喜好,尽管仍有一些反感是因人而异的。
一旦选好走哪条路,焦虑就烟消云散,顿时我又满心喜悦,只想塑造香水,谱写香水。但焦虑偶尔还是会在最后的择时刻回来。
-
Shaza是 iPhone的一款音乐辨识软件,在上面几乎能随时找到歌名和曲名。这款软件神乎其神,但也有些无损于它的优异性能的局限。这一晚,我听着电台播放勃拉姆斯,却想不起曲名,我马上求助于这个软件。我的请求失败了。 Shazam无法满足我的要求,因为那场录音是在公共场合完成,并未收录在任何唱片中。既然没有标记,就无法辨识。 Shazam可不懂什么是“差不多”。
从隐隐约约的线索中去猜测,是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做的事。我漫游巴黎时,自然不认识每条路,但是凭着视觉上的揣测估计,幸得某间商店、纪念性地标、某建筑物的特征,或偶尔凭着嗅出面包店、杂货店的气味,我就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街上闻到的香水味亦然。远远嗅到熟悉的香水留下的余味,我便能认出形式,越是靠近,细节就越是挥之不去。
-
我回到工作室,来到我亲爱的瓶瓶罐罐身边。我不在的时候,留下一份主题为梨子的配方草稿有待斟酌。柔和翠绿,无比诱人。我在梨香中掺入花香调,不带白花特有的累赘、麻醉的特征,以及广藿香、木质香及劳丹脂组成的西普谐调;后者应该会在香水的酝酿过程中,犹如弹奏出的一小段乐音。写下这几个描述香水的字眼时,我意识到自己才是唯一能在脑中呈现这个味道的人。或许我可以在这本日记里,揭露一些调香师才能破解的密码。只是说归说,把我脑中的香水结构交出去,阅读日记的人也不会更明白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在演进。我无法预知过去的经验能起什么修正作用,亦不能预见未来。
-
化妆品业使用的原料的质量固然是关键。质量即承诺,务必讲究,因为它是香水的一部分,而且绝不能成为左右创造性的借口。最上乘的原料未必能制出一流的香水。
十月的香柠檬精油,其品质与十一月、十二月、一月或二月的香柠檬精油别有异趣。制作过程需要五个月,生产出来的精油有绿意、活泼、清爽的前调,紧接着是花香及甘鲜美韵。在十月的香柠檬精油中,有大量
具花香的分子芳樟醇;二月的香柠檬精油芳樟醇含量很少,却含大量具清新香气的乙酸芳樟酯。然十月的精油因为有微量的叶醇,闻起来却有清香。在二月的精油里,叶醇和芳樟醇隐微不彰,让乙酸芳樟酯大大占了上风。大自然玩弄我们的鼻子,十月精油的花香和二月精油的清新只有在调配香水的时候,才分辨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