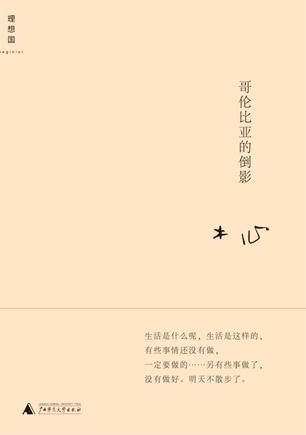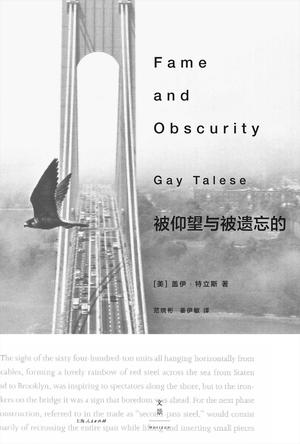-
所有这些情景,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快车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权指责他们吗?他们想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乐,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感到现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去享受,穿几件好衣服,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有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
就像大家总是说等疫情过去要怎样怎样,但当大家意识到疫情或许不会那么快过去,就毅然决然地去实现之前所说的愿望。这不是软弱,不是意志不够坚定,这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态度。
-
所有这些情景,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快车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权指责他们吗?他们想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乐,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感到现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去享受,穿几件好衣服,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有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
就像大家总是说等疫情过去要怎样怎样,但当大家意识到疫情或许不会那么快过去,就毅然决然地去实现之前所说的愿望。这不是软弱,不是意志不够坚定,这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态度。
-
善良的图尔人除了报上登的消息外,并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刚看到威廉皇帝,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感到十分吃惊,不由得惊恐万状。我觉得,经过多年对德国仇恨的宣传,流毒已浸入平民百姓的心里。在这个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这里的市民和士兵毫无恶意,却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有这么大的仇恨。银幕上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画面,就引起这么一场骚动,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可见流毒是多么深广。下面继续放映其他画面时,他们就把刚才的一切忘记了。当晚放映的主片是一部喜剧,观众看得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有人乐得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那仅仅是一秒钟,而那一秒钟却被我看到了。我们曾做出过不少努力,想方设法促进国家间和民族间的谅解。可是到了关键时期,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被煸动起来啊!
在这非常疫情时期,每个人都被卷入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我身边的人们看似忙于生计,工作不休,但他们会在工作间隙似笑非笑地突然诘问我:“你说美国人为什么非要说中国病毒?”“你说美股熔断了这么多次,美国人为什么还没把特朗普赶下台?”这样的事情一周之内发生了好几次,终于让我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期待我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认真回答他们,他们只是想要向着一个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发泄他们心中的情绪。这种状态就像夏日午后的阵雨,突如其来,过去得也很快,连水渍都被炎热的阳光蒸发得一干二净,或许这场骤雨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些松懈的快适也说不定。
罗曼·罗兰在这段后面的看法很有趣:“百姓越老实,就越容易轻信。”
-
我初次结识这座城市的时候,它还不像今天这样,有地铁和各种汽车把城市连接成一个整体。在当时,巴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浑身冒热气的肥壮的马匹拉的厢式马车。从这种马车的第二层,即顶层上观看巴黎,车速缓慢,是再好不过了。那时候,从蒙马特到蒙帕纳斯去一趟,算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觉得那些关于巴黎小市民节俭的传闻是完全可信的。他们舍不得花钱去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所以,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人,从来不到右岸去;有些孩子只在卢森堡公园里玩,却从没有去过远处的杜伊勒里公园和蒙梭公园。在马车时代,车费是小市民必须考虑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市民或者老巴黎人最喜欢蛰居在家,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在大巴黎内部创造了一个小巴黎。所以巴黎的每个区域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甚至有不同的地方色彩。
笑哭。这不是上海么?
-
我见到了范·德·施塔彭,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几乎已经消失。不过这位身材矮小、面颊红润的佛来米人倒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与他的夫人,一位高大宽肩开朗的荷兰人,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年轻人,给我看他的作品。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的文学和艺术。他们的善意打消了我的所有顾虑。我不加掩饰地对他们说,我到布鲁塞尔来就是想见见维尔哈伦,恰巧他不在。我很遗憾。
是否我讲的有点太过分了?是否我讲的有点憨直?反正我觉察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对视一笑,偷偷使了一个眼色。我觉得我的话引起了他俩会意的默契。我感到很不自在,想告辞。他们执意留我吃午饭。他们相互使着眼色,一脸神秘的微笑。不过我觉得,即使有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友好的,于是我放弃了去滑铁卢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们已经坐在餐室里——像所有的比利时住房一样,餐厅是在一楼——透过餐室的彩色玻璃可以看到临屋的一条街道。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餐室窗前,听见有人用手指敲玻璃,同时门铃也突然响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说着就站了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他”是何人。但门已打开,他迈着沉重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原来是他,维尔哈伦!我一眼认出他,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他。维尔哈伦是这里的常客,今天凑巧也到这里来。所以,当我说出我到处找维尔哈伦而不得见时,施塔彭夫妇迅速地使眼色会意:不告诉我,给我意外的惊喜。现在,维尔哈伦已站在我的面前,施塔彭夫妇对刚才的小玩笑得意地微笑起来。
太可爱了,太明媚了!从一开始的求而不得,到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光是看这段文字我的内心就起伏了无数次,最后忍不住想要开心大笑起来!
先是担忧说话直率不加掩饰的年轻人无心之言得罪了别人,只是大家都用善良的心态包容他,然而话锋一转,这些可爱的人不仅善良包容,而且是对待年轻艺术家报以绝对热忱的真好人!
也许施塔彭在艺术史上的名字已经被时间的浪潮逐渐抹去,但他在茨威格的文字中得以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