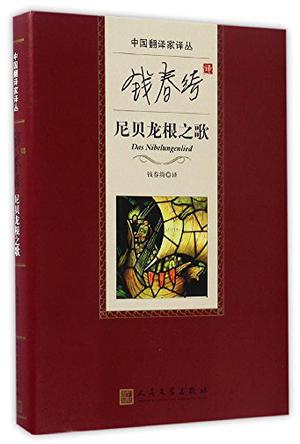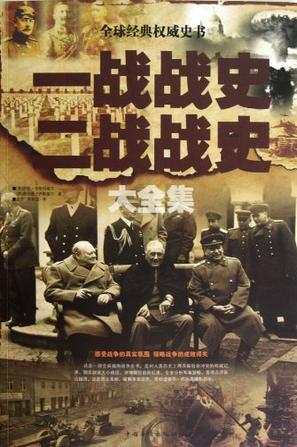-
他们两个都往那个老太婆那儿瞧,我也跟着往那儿瞧。虽然那天很暖和,她好像一心一意只想烤火。在我看来,她连火上的汤锅都有些炉忌;现在想来我深信不疑,她眼睁睁看着我硬逼着那炉火为我服务,给我煮鸡蛋烤咸肉,她愤愤不平;因为,在这种烹饪正在进行而又没人看着的时候,有一次,我那双惺忪的睡眼看见她对着我晃了晃拳头。阳光从小窗户射进来,但是她和那把大椅子都背对阳光,她把炉火屏蔽住,好像她尽心竭力在使炉火保持温暖,而不是炉火使她保持温暖似的,而且以极不信赖的态度望着炉火。我的早饭做完了,她见火空出来,非常高兴,因而大笑一声——我得说,她那一声笑,非常难听。
-
太阳终于出来了,我的旅伴们睡得舒畅了一点。他们这一夜,鼾声如雷,嗝声不断,睡眠之困苦简直难以想象。太阳升高了,他们的觉睡得也了,于是一个一个地醒来。但人人都推说自己没有睡过,谁若说他睡了,他便怒不可遏。这种情况,我当时十听了,感到诧异,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困惑不解。我不明白,在人类所有的弱点中,为什么我们最不甘心承认的弱点,竟是在车里睡觉这件事呢。
-
时值仲夏,夜晚凉爽宜人。车从一个村庄穿行而过的时候,我便想象农舍里是什么样子,人们都在做什么;男孩子们跟在车后奔跑,攀到车上,抓着车悠荡一会儿,这时候我就猜测,他们是不是也没有父亲,是不是在家里也不快活。这类事儿我想了很多,此外就是琢磨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不去想别的,只想家和佩戈蒂;要么就是模模糊糊地想,我咬摩德斯通先生那一口以前,是什么心情,那时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但想来想去,茫无头绪,我咬他那一口好像是远古时代的事了。
-
我难以给别人一个清晰的概念,表述那五天究竟多么漫长。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占据的,不是五天的地位,而是若干年的地位。我侧耳倾听家里切可能听见的琐细动静,如铃响声、门开合的吱喽声、喃喃说话声、上楼(的咯噔声;细听外面的人的笑声、口哨声和唱歌声,在我那样的孤寂和耻辱中,这一切都显得比任何事物都更难堪。时光行进的速度令人捉摸不定,特别是在夜间,我醒来时觉得该是早晨,却发现家人还没有就寝,漫漫长夜才刚刚开始。夜里我常常做些噩梦,受魇魔纠缠,弄得我意气沮丧。清晨的中午、下午和黄昏来临,别人家的孩子在教堂墓地里玩耍,而我却只能在屋算子里远远观望,满心的惭愧使我不敢在窗口露面,唯恐他们知道我是个囚犯。我老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不免感到奇怪。有时见有吃的、喝的瞬间仿佛觉得高兴了,但吃完喝完了,又懊丧起来。有一天晚上,下起雨来,带来清爽的空气,雨越下越大,把我和教堂隔断,雨和昏暗夜色好像把我淹没在阴惨、恐惧和悔恨之中了。这一切的一切,周而复始,好像不是轮回了几天,而是轮回了若干年,从而在我记忆中留下那样鲜明、强烈的印象。
-
开始就来了这一手,对我的镇定不啻是一贴清新剂。我觉得我功课里的字全溜走了,不是一个一个地溜走,也不是一行一行地溜走,而是整页整页地溜走了;我倒是想抓住它们,不许溜走,可是,如果我可以这样比方的话,它们都好像穿上了冰鞋,飘飘然滑走了,想拦也拦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