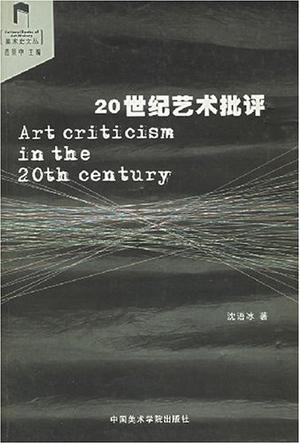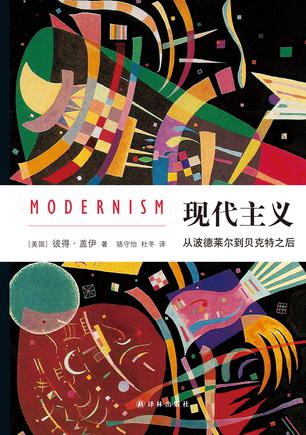-
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是施展一个“金蝉脱壳”计。
父亲一旦提笔画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那种享受感、陶醉感,与平常判若两人。
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金蝉脱壳”了,特别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频繁,外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神游青山绿水之中,在艺术世界中徜徉……以至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是上天的恩赐,否则的话,他老人家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
我对父亲的仕女画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是因为在母亲生我的那一年,父亲画了一幅很大的仕女画《山鬼》。画面上风狂雨骤,一位神秘动人的女子,在虎豹的环伺下,游于巫山之顶。见过这幅画的人,无不被这画中的灵氛所笼罩。父亲自己在画完之后也不禁惊叹:"似真有鬼也。”每当我面对这幅《山鬼》,总觉得那女子在对我说什么,有招引我前去之意,使我惴惴不安。
《我的父亲傅抱石》
傅益瑶
-
明初有位以画华山得名的画家王履,他在《华山图序》(现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里很尖锐地批判了所谓“写意”(主要是山水画家),说:“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画物欲似物,岂可不识其面?”(王履《华山图序》,《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六引《铁网珊瑚》),这是针对盲目的打倒形似追求“写意”的恶劣的形式主义倾向而提出的。像他画华山"苟非识华山之形,我其能图耶?”(同上)他这样坚持从现实出发来画华山是正确的,可是形式主义的倾向明初已经抬头,所以他在“序”的最后好似指着《华山图》厉声地叫着:"以为乖于诸体也,怪问何师?余应之曰: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
-
郭熙曾经具体而严肃地号召山水画家一切向“真山水”学习,要画家们走到自然中去,这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基础。他认为只有不断地从真山水观察、体会之中,然后“山水之意度见矣”。所谓“意度”,当然不是指的“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客观描写,而是指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自然的融合乃至季节、朝暮、晴雨、晦明…诸种关系的总的体现。同时,这总的体现又必须是内容和形式高度的一致。他说,“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因为山水是“每远每异”“每看每异”的,“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侧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所谓山形面面看也”。他要求山水画须具有“景外之意”和“意外之妙”(以上引文均见《林泉高致》),即是山水画必须赋自然以丰富的内容,同时又必须赋自然以真实、生动的形象。
-
从相当丰富的五代山水画遗迹(大部分虽是传为某家的)研究,“三远"——高远、深远、平远——的方法,毫无疑义是中国山水画卓越的天才的创造。这样来处理画面上的空间——远近的关系,实在是体现自然唯一合理而正确的道路,也是现实主义传统的表现形式和技法道路。人在大自然中,除了平视,不外是仰观和俯察,“三远”的方法,恰恰就很完整地具有这些内容。宋代有一位山水画家郭熙,曾经明确地解释过“三远”,他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郭熙《林泉高致》,《佩文斋书画谱》卷十三)“三远”的方法不仅仅是单纯地解决了空间关系的基本问题,重要的还在于以此为基础发展并解决了许多使用和鉴赏形式的问题,亦即如何更好地表现主题的问题。我们了解,直幅和横幅,一般的横幅(所谓横披)和长卷,它们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特别是长卷的形式,彻底地说,它的空间关系,是以“三远”为基础同时又是“三远”综合的发展。像前面所谈到的《清明上河图》卷,作为山水画看,也是可以的。若机械地使用"三远"的远近方法,绝不济事,必须灵活地融合创作、鉴赏的实际为一体,一切为主题服务,才能够把大千世界变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品。
-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缙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所当学也!
——《画旨》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家有南北二宗,亦
唐时始分。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而为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
大家
——《画禅室随笔》
董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