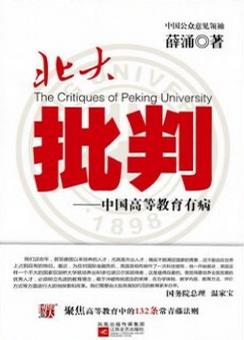此书摘本创建于:2016-11-02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最新力作,总结多年探讨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之思想成果
★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求解中国人的正义诉求与幸福生活来源
★附赠作者亲绘课程配套全彩“心智地图集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汪丁丁
-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 定价:99.80元
- ISBN:9787208114708
-
回顾民国初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废除君主制之后,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在“混乱”和“利维坦”这两个极端情形之间徘徊。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按照通常的理解被分为“国家工业化时于期”和“市场化”时期,这两个时期之间有10年的混乱时期。也是按照通常的理解,在国家工业化时于期,国家扮演了经济发展的主角。因此,伴随着工业化的,是经济计划和正规管理的官僚化过程。在“三反”运动之后,毛泽
东试图通过诸如“打破讠计划平衡”和“干部下放劳动”这样的方法缓解官僚化,但效果甚微。“文革”之后,效率原则再度成为重要社会成员的共识。因此有了30年的市场化时于期,最富于企业家能力的各种群体扮演了经济发展的主角。在30年市场化的最后10年,主要由于政府寻租的激励,官僚化倾向再度占据主导位置。目前的情形是,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或超过“民主诉求”的阈值,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两方面压力联合作用的结果,很容易导向“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虽然长期而言,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难以为继。
另一种政治演化路线,就是推行“政治民主化”,将权力交给人民。通过极大地强化“民权”来压制官僚垄断利益集团。但是,这一路线要求人民有足够强烈的公民意识,要求精英及强势群体足够地自我节制,还要求有一批政治影响力足
够大的“中介”得以维系社会稳定性(实践智慧)。为克服这些困难,相当多的鼓吹者认为应首先推行“党内民主”。其实,不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关键是最先获得民主权利的人必须有足够强烈的公民意识。多年前有人建议的人大代表“职业化”,不失为一项好的政策。职业化(类比于法官薪俸独立于政府)的人民代表,如果由本区竞选产生,则本区公民的意识足够强烈;如果由全国竞选产生,则中国公民的意识足够强烈。 -
使上述状况更加恶化的是:(1)金钱与权力勾结导致的普遍腐败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如果“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999,却只有美国总产值的1%,那么中国很可能更糟糕;
(2)社会保障系统的普遍缺失——这是事实,尽管政府已付
出了很大努力,但中国社保系统将面临远比美国严重的财务危机;
(3)失业救济系统的缺失或不足一—如果一个人有获取收入的能力,却因为失业而在短期内没有收入,也就是他的生命周期里面积B的损失,通常应由失业救济补足;
(4)劳工阶级组织自由工会的合法权益基本缺失—成熟市场社会里,工会在改善劳工收入方面至关重要,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工会的存在可使失业率上升。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劳方由于不能有组织地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借助罢工威胁),因而他们的工资很可能低于市场工资。换句话说,中国的工资不是自由市场的,而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
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由于官僚子弟对全部稀缺资源的独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成为让官僚子弟先富起来的政策。虽然,更确切而言,让控制稀缺资源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中国目前的情形就是,企业家能力在政治与寻租领域的创新活动的收益与成本之比,远远超过了在经济与市场领域的创新活动,而且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从全国和地方的历届“两会代表”(政治寻租领域)的人均收入或人均财富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间接地推测这一状况。
随着社会的官僚化趋势的增强,由一系列偶然性导致的政策建议或社会选择的“议题”,现在被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取代了。这些官僚机构的典型工作方式是“文牍主义”。
官僚机构为要迅速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首先要收集和处理并理解正确应对这些问题所需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分布在社会网络的少数局部,则依靠官僚机构求解社会问题的信息成本就比较低。但是,这些信息通常分布在社会网络的许多局部,这时,官僚机构的信息成本就会非常高。 -
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掌握文化权力的群体(知识分子)履行社会批判的职能。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普遍“左倾”,就是因为他们要批判社会主流,而主流是市场的(右倾)。诚如福柯所言,启蒙就是对主流保持永恒批判的姿态。可是,在中国,形成了一种被社会学家(孙立平和李强)称为“全能集团”的强势群体。这一群体垄断着全部三种权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一局面非常危险,因为社会因此而听不到批判的声音—对权力的批判和对金钱的批判。更长期的危险在于,原本应承担社会批判职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完全消失了。
我们环顾四周,有知识的人很多—教授、记者、作家、演员,他们并不批判社会,并且努力要进入或迎合社会主流,所谓“同流合污”。这一趋势导致中国社会严重的并且迅速恶化的两极分化。严重的两极化可能导致革命。预见到革命
的毁灭性后果,执政党可能实行改革(改良)。
请回忆赫费的著作《政治正义性》,人们之所以赞成利维坦政府,是因为霍布斯丛林战争的痛苦体验超过了独裁可能有的代价。这样,社会就从民主进入独裁,独裁统治下的社会,可逐渐恢复秩序,这是独裁者对社会的承诺。独裁是可能长期维持的,如果独裁者兑现了关于社会稳定性的承诺,并且使社会为独裁支付的代价(通常与腐败有关)控制在较低水平。
中国在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下完全丧失了“社会”,于是不
得不在改革开放时期将“社会”重新生产出来。
沈原领导的清华社会学系“农民工”课题组,最近在《新世纪》周刊发表了农民工研究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以及沈原的文章,他说那些农民工的子弟,最初或许是有理想的,但在职业中学的教育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现实”,男孩子在毕业时最高的预期就是“门卫”或“保安”。 -
宗法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为什么没有恢复宗法社会之可能呢?显然,这套纲常与效率原则有激烈冲突,故而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难以为继。但是,其次请回忆,中国宗法社会还有余英时阐述的那种内在超越式的人文关怀。在这种人文关怀的指引下,中国人可以从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满足,而不必纠缠于社会生活维度的纲常伦理。我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于那些真正获得了内在超越能力的中国人,至少在他们追求精神自由的初期,纲常伦理反而成为严重的束缚。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路径在从物质生活的温饱阶段转向社会生活的深层情感交流时发生的问题。这一问题不得到解决或缓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来源就依旧只好停留在物质生活维度之内,从而导致醉生梦死的人生观和纸醉金迷的日常生活。罗马帝国末期如此,中华帝国难道不能有如此的末期吗?
我要澄清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的涵义。在英文中,生活方式是 the way of life,已经包含着情感和精神生活。但为要强调我们中国人遇到的基本问题,我特别地使用了“情感方式”这一短语。我的解释是,情感方式是由内向外地体悟而获得人生之意义,这样一种认知过程典型地是传统中国士人的,而不是西方的。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困境在于,我们不是任何传统之内的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推毁工
因此,由表及里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内向外的是我们的情感方式。我们每一个人以这两种方式生活,或许有偶然的机遇,可使我们由表及里的过程与自内向外的过程顿悟为一。但这样的机会太少,遇见这样机会的中国人太少。绝大多数中国人无缘顿悟,只好在日常生活中寻自己的幸福。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一样,是迅速西方化的。退居深山的生活不是日常生活。西方化或工业化或效率主导的日常生活是物质的,同时,我们还有自内向外的探索,目的也是寻自己的幸福。 -
我记得一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到夏威夷大学读博士学位,每一次见到我总是重复一句话—“ Meaningless”(毫无意义。)我问他为什么无意义,因为哪些方面的事情,不得而知,甚至连回答我的问题也显得毫无意义。
182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循环往复。然后是革命党夺取政权,继续循环,直到最近一次,称为“后文革”时期,也称为“改革开放”时期。在100年时间里,我们在物质生活维度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另外两个维度的情况,尤其是精神生活维度,则很难说有很大进步。所以,过去100年的演化过程,我称为“效率原则”主导的时期。仅仅有足够高的效率,不能解决每一个中国人面对的基本问题。例如中国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1/4,并且,中国的腐败指数远高于美国,结果,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恶劣状况就远不是“人均收入”可以刻画的,也不是平均意义的基尼系数能够刻画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今天感受最深的,是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和财富与收入的不
平等,尤其是不平等程度正在迅速扩张。
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深层情感交流”的能力。写到此处,
我想起一位朝鲜的亲戚,她是我岳母的表侄女。2003年,她历尽艰辛从平壤来到北京,住了几个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白头山传奇”,特别记录此事。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
这篇文章—白头山就是长白山。我的印象是,她看电视的时候只是流泪,几乎完全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朝鲜的日常生活,远比我们经历过的“文革”时期更革命化和军事化。我们在“文革”时期养成的习惯就是尽量不表达甚至要消灭个人情感,因为这类情感是小资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只经历了“文革”十年。而朝鲜消灭个人情感的时期,至少长达两代人(从金日成到金正日)。难
怪这位从朝鲜来的亲戚,在自己母亲的姐姐面前也完全不会用语言来表达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