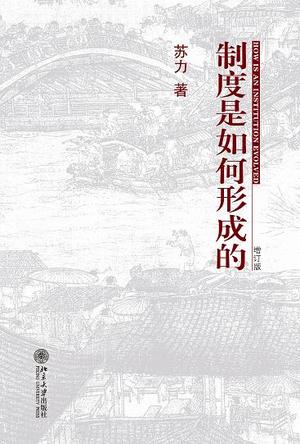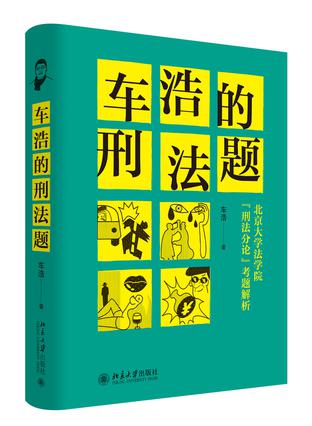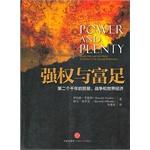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3-17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大致分成三编。第一编主要是关注一些社会和法律的热点问题,诸如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婚姻法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送法下乡、科技与法律以及司法审查 …… [ 展开全部 ]
- 作者:苏力
-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定价:26.00元
- ISBN:9787301126820
-

-
这就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候,法学家并不是有了充分的理性准备来接受社会界定为“法律”的那些任务,而是被社会“强加”的;强加给他/她只因为现代社会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将他/她标记为法官、律师或法学家即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推定和认定他她有这种能力,而不论他她是否真的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具有能力。因此,法学其实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是一门仅仅熟悉法条加秉公执法就能完成的精确的或形式化的“科学(未来是否能够精确起来,我也很怀疑),而必须以一种似乎很精确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实际上无法精确处理的问题。“清官难断家务事”可以说是中国古人对这一点的最深刻的理解和概括。我在此说这些话,固然是渴求社会的理解,却决不是想推卸法律人的责任。相反,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或对应的“法条在那里可供套用,可以作为退守的堡垒,因此,法学家才必须更注意社会实际注重吸收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人情世故和常识,才可能大致越必定不会令所有人满意地履行他们的使命。法学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形式化、条文化的学科,尽管人们想象中的法学面目恰恰相反。
-
因此,法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务实和世俗。世俗并不具有贬义,而只是说它的基础是社会现实,它必须始终关注现实,回答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关心的常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是一种非常讲求功利的学问。它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在很大程度排斥独出心裁和异想天开。它有时甚至不要求理论,而只要求人们懂得如何做。这与文学和纯粹的思辨理性也有较大差异。对文学艺术作品甚至就要求其在“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语),甚至别人都看不懂也行;一个理论也可以天花乱坠,只要其足以自洽就可以成立,对于社会的其他人来说,并没有太大关系,最多是小说和著作无法出版,或读者很少,出版商赔本而已。而且,读者的一时多寡也未必就能决定小说或理论本身的价值(因此对“经典”的某种黑色幽默界定是,经典就是人人都承认应当看却都不看的著作),因为这些都是高度个人化的创造性的事业。而法律人的事业有很大不同,他/她从事的不仅关系自己的个人收入,其一言一行更可能决定别人官司的输赢,别人的身家性命,别人的一笔财产的归属,一句话,他她直接决定着别人的命运。相比之下,法学院教授比他们的职业性同伴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容许有更多的智识性创造。但是,法学的研究也仍然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制度乃至社会制约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各个法律院校中,修法哲学、法律史课程的学生一般总比修民法、刑法的学生少,而且也更不情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诸如马克思、韦伯这样的天才创造性的思想家,尽管毕业于法学院,并且都有家学渊源(马克思父亲是律师,韦伯父亲曾是法官),最终却都走上了社会思想家这条不归路的原因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其他某些学科可以甚嚣尘上,在法学界,偶尔也有理论法学家“蹦跶”几下,但是对法律实践的影响甚小。这就是学科的知识制度的制约。
-
这并不意味着,法学不能在某些时候作为一种有意图的工具来推定指控是否成立的动社会的变革。的确有这种情况,并且时而也有成功的例子。但就总体而言,即使成功也不是法学本身造就了这种成功,而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这种法学或法律;或者是以法律名义的国家强力起了作用。然而,即使是后者,法律能否真正成功,能否真正为人们接受,仍然不是利用法律推进改革的政治家或法学家能保证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公共选择;例如人民公社制就曾进入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但终究被公众否弃了。法律,在这一点上,如同社会中的语言,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天才的创造,而是公众以他们的实际行动集体塑造并在行动中体现的。即使是一些表面看来重大的法律规定的变革,就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规范作用来看,意义也未必那么重大(其意义往往是成为一种符号或标志)。因此,尽管《拿破仑法典》被公认为是法律史上的一大变革,但是法典起草委员会主席说的话大意是,“既然现在人们都喜欢新,那么我们就给他们一些新理由来喜欢旧法律”(所谓旧,只是指当时社会已通行的而已)。而且,现代法治的
项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法律不能规定人们做不到的事;其中的寓意就是任何法律规定都不能太脱离实际的“新颖”。
由于法律和法学的这种保守性,因此,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一些“精英”或“先知先觉者”往往会感到社会中法律的发展似乎总是与他们感受的时代潮流“慢半拍”,甚至感到法律制度本身就是压制性的(例如,福柯的许多研究中都显现了对现代法律制度的激烈批判)。的确如此。首先,就总体而言,只有在社会秩序基本形成之后,才会逐步形成一些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也才有必要将这种秩序以法律固定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法学的研究才发展起来在革命时期,在高速变革时期,法律和法学的发展往往会无所适从,就会出现停顿,甚至萎缩。即使人为努力制定法律来保持秩序,也未必能够成功;反倒可能出现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的悖论。其次,即使在和平稳定时期,由于法律要求的对人对事的普遍性,它也势必不能“朝三暮四”或“朝令夕改”,它不是以其“先锋性”满足社会的革新者(这种人一般说来总是少数)对于未来的畅想,而是以它的“老规矩”“萧规曹随”来满足社会多数人对可预期生活的需求(一般说来,只有当社会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生活的实际规则都发生变化时,法律的变化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才说出了那多少令我们这些法学家有些迷惑不解、不快甚至羞于引用的话:“法
…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 -
但是,即使弱者也有其“长项”。一旦社会进入比较稳定的时期,特别是社会分工发展了,社会的交往、交易增多了,社会对规则的需求和依赖就多了,法律也就有了其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正如贵族公子落难乡间可能洋相百出,一旦进入上层社会,他则可能风流倜傥,挥洒自如。法学似乎就具有的这一特点,并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不仅见诸于西方各国历史(例如,如今挤也难挤进的哈佛法学院当初有年只招到一名学生),而且在当代中国,似乎也可见端倪。分数最高的文科考生,20年前大多报考文学、哲学、外语,而今天则大致报考法律、经济、管理;尽管就学术传统的扎实和久远来说,后者至今未必是前者的对手。而且,尽管经济学今天在中国似乎很热,但这种情况未必会持续下去。至少在美国,经济系已远远不如法学院、商学院兴旺。似乎是盛洪告诉我的,科斯说过,美国的法学家比经济学家更有能耐,因为前者可以不断地为自己创造市场需求和职业。当然,创造市场只是方面,另一方面,这也是稳定社会中分工日益细致、交易日益频繁、规则日益增多的必然结果。
不要以为我是在洋洋自得,以一种尚未成为现实、在中国未必会,且未必应当成为现实的畅想来满足因被学界评价为“幼稚”而受到损害的职业虚荣心。我仅仅想指出法学自身的特点。只有发现其特点,我们也许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法律行当为什么目前开始发达起来,法的口号会流行起来,法学教育会膨胀起来,而法学的发展似乎又不如人意(以致被人耻笑为“幼稚”),以及为什么法学家似乎目前总急于参与立法或注释法条,似乎缺少一些学者应有的开阔视野、博学和社会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