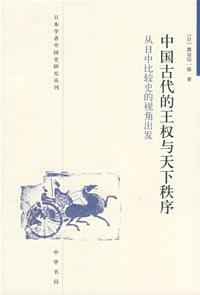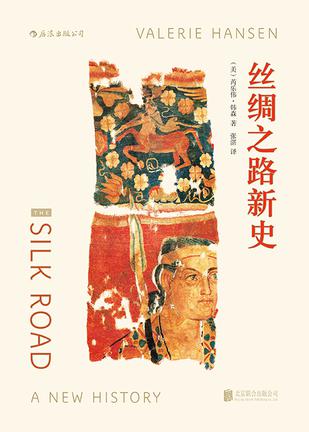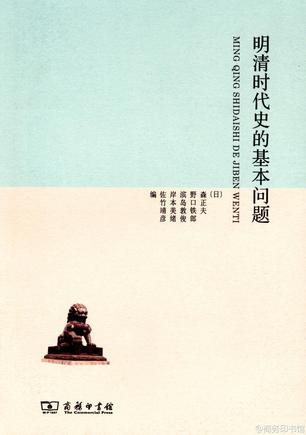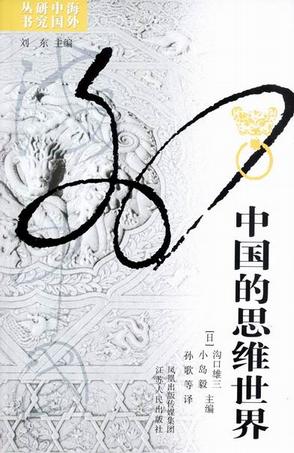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3-06
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
对比于源自欧洲的概念“国家”、“帝国”等,作者择取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词语“天下”作为关键概念,从“天下”的意识形态结构、“天下”的领域结构、天下观念与中国古典国制的成立以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渡边信一郎
- 出版社:中华书局
- 定价:46.00元
- ISBN:9787101062410
-
也有必要注意圜丘祭天仪礼参列者中包括了来自国内各州的使节团(朝集使)与外国使节团(诸蕃客)。可以说这正是《孝经》所述“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的实现。对于整然的天之秩序的祝祭将以皇帝为中心,由九品官人(中央官僚)、朝集使(地方)诸蕃客(外国)组成的地上全体政治
秩序,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同时展演出来,从而可与天之委任互相呼应。详细论述参考渡边的另一篇文章,《元会的建构》,已有笔记,不论。 -
沙州的“西汉金山国”白衣天子,与以甘州为根据地的回鹘天可汗冲突不
断。但是两国之间,订立有以天可汗为父、以白衣天子为子的盟约。《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载,“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又在曹义金给回鹘宰相的回信里也说,“况众宰相先以大王结为父子之分”(《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伯希
和文书2992)。相比于领有天下的唐之天子太宗与尊太宗为天可汗的西北诸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不过只是蜗牛角上的争夺,完全可以看作儿戏一般。但是这一以汉人天子为子、以异民族君主为父的盟约,却成为以后契丹与后晋之间的盟约(割让燕云十六州,契丹为父,后晋为子)、辽与北宋之间的盟约、以及领有华北的女真族之金与对金执臣下之礼的南宋之间和约的先声。
从西北边境烽火台中传达出的“西汉金山国”白衣天子的十年,是象征性表现出中国王朝(天下型国家)与周边诸民族(蕃国型国家)之间新型关系
成立的事件。前面已经提到,渡边的问题在于视野受限,从后记来看,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日本历史学家对于“非汉”民族王朝的关注远甚于中国人自己,从游牧民族角度切入中国历史不能不说是个冲击,其实也没必要大惊小怪,太过担忧,学术研究又不是吵架,比谁的嗓子大,比谁的论点“高调”,回到本书,契丹-辽的崛起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意义非凡,较为详细的论述还是要参考杉山正明的研究,“大中国”使得中国真正能够与今日之中国发生关系,而北宋时代的观念还是需要我们细细思考,关于这点,葛兆光的论述有所启发但是我觉得言过其实,所谓现代民族国家之类的能否达到这样的状态,实在不好说。 再,渡边此书可以深究处很多,这就是说可以深入研究的更多,难得的一本好书,可惜论述还是太少,整体创见不多,不如他的另外几篇专题论文,另见他文,此处不论…… -
本章的目的,是藉由对围绕天下的领域观念的考察,来明确古代中国独特的国家观念的特质。以下,就回顾一下本章所得出的几个论点,同时指出天下型国家及在其外部被构想出的世界观的特质。
如果系统观察中国古代经学上的天下观念,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三种基
本认识:①《礼记·王制篇》将领域方三千里的九州=中国作为天下;②尚书》今文经学将方五千里的九州=中国作为天下;③《周礼》、《尚书》古文经学则构想了由九州与四海(中国与夷狄)所组成的方万里的天下。这些被构想出来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扩张了的古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实态,也构成了在其后的传统中国中应该不断作为参照的典型。
与天下相关的三种基本认识,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将天下理解为由同一语言圈、同一交通圈、同一文化圈所构成的九州=中国这样的单一政治社会,这是今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一种将天下理解为包含中国与夷狄在内的复合型政治社会(帝国),这是古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天下同时具有这样的单一政治社会型侧面与复合政治社会(帝国)型侧面,为传统中国所接受。但是,如果从专制国家基于郡县制对编户一百姓施行实际支配的实态来反观天下观念的话,可以说这两个侧面虽然在不停地相互转化,却是向着单一政治社会回归的。单一政治社会型面貌与复合政治社会型面貌,是天下观念的两个侧面;但是其决定性的侧面则在于单政治社会型面貌。这一点在前章中已经藉由唐代的事例被验证了。可以把这种天下观念与实际支配结合而成的综合政治社会样态定义为天下型国家。
基于传统中国皇帝支配所具有的实际支配与意识形态支配这两种支配的相互关系是向单一政治社会回归的原因。
传统中国的皇帝支配,是通过户籍而实际达成的。即对于具体个人,将其作为百姓把姓名与居住地以家族和家庭为单位固定于户籍之上,再通过郡县的行政机构与经济性收取机构而使其隶属;藉由这样的制度来达致支配。通过户籍达成的皇帝的国家支配,是特定了其被支配者是何处之何人后才成立的,其本身就是有限的。因此,天下作为皇帝(天子)所达成的统治领域,本来也就是有限领域,即被限定于郡县制所及范围之内。
传统中国的皇帝支配所具有的另一侧面,是以德治来进行支配,即藉由意识形态而领有被支配者的能动意志。如《孝经·天子章》所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唐玄宗御注对此解释说,“则德教加被天下,当为四夷之所法则”,邢昺之《疏》也引申说,“如此,则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当使四海蛮夷,慕化而法则之”。德治,不止是支配天下之百姓,也及于四海之夷狄。正如前面所说的,天下观实际上是一个假象,至于天下秩序也多是松动的一种状态,在古代中国,皇权作为政治的核心,以它为中心的政治构造是受到多方限制的,中国之所以不是扩张性的帝国形态,解释的角度很多,但是中国逐渐形成的对“天下”的认识也是重要原因,从封建到郡县一般被称为周秦之变,这才是真正的千年大变局,古人争论已经很多,此处不再赘述,但是讨论多集中在统治结构,也就是中央集权,另一个方面伴随中央集权而来的被迫要舍弃的一些因素却被忽略,稳定性便是其中之一,当然,讨论中国稳定性的更是太多,例如超稳定结构等等,但是结合“得与失”的一种必然性却是太生硬了。 还是回到“支配”上,渡边实际上已经触摸到了中国古代体制的一个关键,可惜他的视角依然限于早期中国,所以有限区域像一个魔咒般拉住了他的视线,中国的突破实际上还有很大的可能,此处不论,关于这个问题,例如大中国和小中国的概念区分、清帝国的统治秩序等都有涉及。 -
 古代经典的指导性意义在日本人这里是被高估的,在中国的现代历史研究中大都又是被低估乃是忽略的。 其实真实性倒是次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进入,这就是态度的问题了,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到了某些领域远比中国人更加深刻的地步,这便是其中之一。礼仪空间、文化意义等解释性的领域是需要一点点温情的,当历史冰冷冷,变得干瘪,也许不是太好,蔑视它无助研究进步,就连“片面的深刻”也是做不到的……
古代经典的指导性意义在日本人这里是被高估的,在中国的现代历史研究中大都又是被低估乃是忽略的。 其实真实性倒是次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进入,这就是态度的问题了,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到了某些领域远比中国人更加深刻的地步,这便是其中之一。礼仪空间、文化意义等解释性的领域是需要一点点温情的,当历史冰冷冷,变得干瘪,也许不是太好,蔑视它无助研究进步,就连“片面的深刻”也是做不到的…… -
天下,是以禹迹=九州=中国这样划定的传统领域观念为核心,以户籍、地图为基础将各个时代所实现的州县一编户百姓支配实体化的实际支配领域。因为是实际支配领域,如唐代前半期羁縻州支配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天下有时也将周边的夷狄包摄入领域之内,呈现出了帝国型的面貌。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我认为应该把带有如下特征的政治社会样态定义为天下型国家:即将九州=中国的编户百姓支配作为其核心本质;同时以在其周围存在通过贡纳关系表明从属的夷狄一异民族社会为条件,有时也包摄了对内属夷狄的支配。
如《序说》中所检讨的,在日本的研究者中,围绕天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其一为山田統、安部健夫氏等的天下=中国说,主张天下主要就是九州=中国;其一为田崎仁義、平岡武夫、西嶋定生、金翰奎、高明士、堀敏一、石上英一、村井章介诸氏的世界说或者世界帝国说,主张天下是无限延展的世界,或者是由中国与夷狄所组成的世界。对此,我通过检证唐代中国的事例,将天下理解为对编户百姓的实际支配领域,设定了天下型国家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以九州=中国为基本领域且有时也可包摄异民族支配在内的政治社会。偏向保守的定义 按,天下这个概念一旦说出来就不知到底是被污名化了还是被民族主义化甚至意识形态化了……